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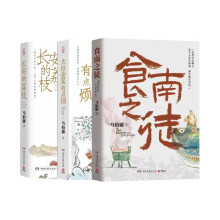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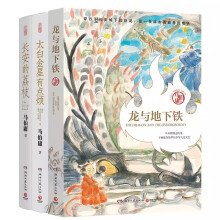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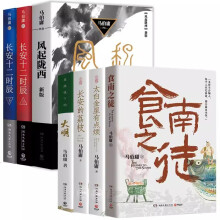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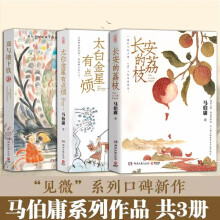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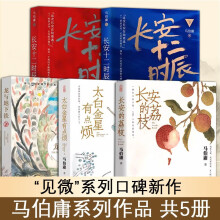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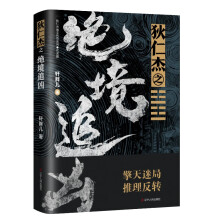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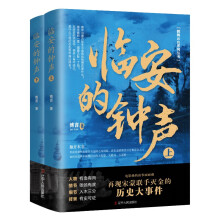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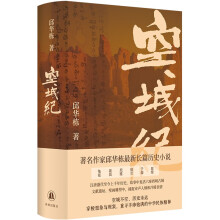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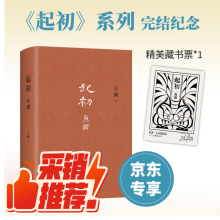
百余张精美彩插,还原小说中铺陈的繁华颓靡,赋予虚构以真实轮廓。
【后记】
为插图本写的几句话
孟晖
能和王非君合作完成这样一个插图本,真的是特别开心。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我一直在逐渐地认识到,限于当初的认识水平,小说里充满了常识性的错误。对我来说最明显的是“桂轩”,按写作时的设想,这座敞轩周围种满了桂花树,在宜王夫妇招待新婚未久的崔文徽与长清县主时,金桂飘香。但是,后来我才明白,唐代文人笔下的“桂”,一般来说,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桂花”,在小说故事发生的年代,不仅洛阳,整个北方地区都没有这种植物。要等到宋代,桂花才作为一种香料植物被开发出来,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关于用香方面的描写也很随意。那时我意识到传统上层生活中有长久而细腻的熏香风俗,但还不懂得它拥有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想必很多朋友都看出,太平公主说赏四种花时需分别焚四样香,是借用了《清异录》中的“韩熙载五宜说”。实际上,感官体验发达到如此细腻微妙的地步,是宋代士大夫文化的特色,并在五代开始成形。唐人则更为粗犷一些,包括在对于香气的品赏上,没有五代、宋时那样精致。同时,在宜王们的生活环境中,能看到的只有牡丹,其他三样观赏花卉都不存在,兰花、荼蘼与木樨(桂花)一样,是宋代的贡献。所以小说中很多地方是把后来时代的生活细节写进去了,只为了制造琳琅缤纷的效果,为了好看。
这些我意识到的错误,此次出插图本时都没有修改,因为一来会造成返工量太大,二来我构思情节时就是这个认识水平,事后修修补补似乎意义也不大。
当然,我还没有认识到的错误肯定更多,这是没有办法的遗憾。
另外,小说中也有一些细节,是我当时就知道不对,但为了好看硬写进去。其中一例是,我那时读过孙机先生的文章,知道唐代并没有中秋节,但为了铺排宜王向柳才人送小饰物的殷勤,还是把这个节日算进去了。当然,这反映的是我对唐代节日不够熟悉,所以不得不挪用后世的节日来充数。
为了出插图本,我也做了少许情节的增补以及细节的变动。即使在这次有限的修改中,我还是忍不住进行了“年代错植”性的借用。最有意的一例是叠璧阁——这个阁名也是我编的——内专设了一间烧香小室。从文献记载来看,这是从北宋中期以后产生的一种奢侈风气,是追求“爇时亦以不见烟为佳”的极致,唐人还没有如此的讲究。毕竟写小说在意的是绘声绘色,吸引读者兴趣,不必像学术文章那样严格。
但有一处,即永宁在高塔上跳舞这一段,好友思伽女史提醒我,他当时跳的应该是胡腾舞,而不是胡旋舞。据穆宏燕先生介绍,胡腾舞“动作以足部的蹲、踢、跳、腾为主”,胡旋舞“以快速不停的旋转而著名”(《舞破尘世升上重霄——从旋转胡舞到苏非“萨摩”旋转舞》)。思伽质疑,在高塔的边沿上很难跳胡旋舞、不断转圈吧?我觉得她的建议实在有道理,所以改成了跳胡腾舞。
还有要说明的是,对于唐代官制什么的,我特别没兴趣,当初草草翻了下相关介绍,就估摸着大概其地给各个人物安了头衔。心里也清楚,以崔文徽的年轻,绝对不该做上五品高官,但是不甘心让他穿青袍绿袍!年轻男人穿红袍才好看是吧!尤其是桂轩一场,宜王穿紫袍,文徽穿浅红袍,一起立在玉栏杆前,这多美……所以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但是实在不好意思厚着脸皮让不到二十岁的永宁也穿红袍,不过好在他穿什么衣服都好看,不穿衣服也好看,甚至更好看。
初版中曾经有个崔文徽暗赠宜王同心结的情节,我觉得有点过于黏腻,就在再版时删掉了。没想到颇有女性读者通过微博等网上渠道表示喜欢这个情节,这让我很意外,于是这次又特意加回去了,是我身为作者向读者奉献上的一点小小殷勤。
在我和王非有意合作,并在微博透露了消息之后,不断有读者——基本都是女性,而且大多比我年轻—留言说期待这个插图本,甚至催促我们快一点,这真是极大的鼓励。《盂兰变》彩绘插图本能够出现,实在与各位相识或不相识的读者朋友的夸赞与鼓励有关,在此说一声谢谢。
孟晖
2016 年3 月29 日
当多数作家读者的眼光集中在明清的时分,孟晖悄悄退到隋唐,遥想帝国初启的开阔气象,眼界已是不同。——王德威
上星期收到一份问卷,问同代的作家中喜欢谁,我想了想,回答,孟晖。——毛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