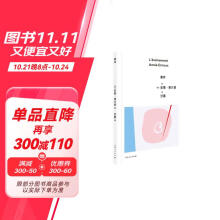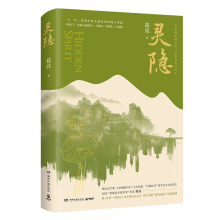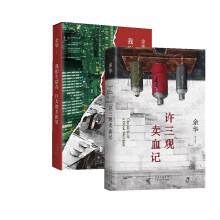《弥补(中经典·第一辑)》: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玛丽被筛选出来,和她的外孙女莎乐美、外孙卡尔曼一起。几天之后,他们死在了奥斯维辛的毒气室里。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我的曾外祖母玛丽通过走向死亡这个行动,将生与死、如今的幸存者与奥斯维辛连结到了一起。这一切,我是最近才知道的。
然而,我的母亲爱莲娜曾经鼓励我听她说一说。
当时我怀着孕,她好像是恳求帮忙一样向我提议:“要是你生个女儿,能不能在她的名字中加上莎乐美?这是我表妹的名字,她什么都没有留下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莎乐美这个名字。
我没有进一步询问母亲。我漫不经心地回答她说:“可以啊。”好像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的儿子出生了,而后母亲去世了,我也就忘记了她的愿望。在母亲所生活的那个世界里,一些人幸存下来,另一些人死去了,我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
二○○三年,母亲去世两年之后,我的女儿出生了。她名叫莎乐美,因为一个女友向我推荐说,“你不觉得这个名字挺好吗?”就这样,我几乎纯属偶然地回想起母亲的愿望。莎乐美降生了,而我则陷入了恐慌。要是我女儿也死了,我怎么能继续活下去呢?
莎乐美的第一夜是在家里度过的,我入睡后很快被第一个噩梦惊醒了。母亲打电话给我。不可能,她不在人世了,这我知道,我在梦中不停地这样对自己说。她坚持着,我接通了电话。我可以向她宣布莎乐美出生的消息了。这会让她非常高兴的。母亲挂了电话。我没来得及和她说话。
我惊醒之后,昏头昏脑,很快又睡着了。这一次,我又梦到一些手里拿着刀的大胡子男人。他们企图打开莎乐美房间的窗子。我推开他们,把窗子关上。他们消失了。我醒了过来,懵懵懂懂,对梦境不得其解。
莎乐美·伯恩斯坦,我女儿继承了她漂亮的名字,她是外祖母的姐妹瑞雅的女儿。
我的外祖母金达一九。八年出生在立陶宛一个有良好教育的犹太家庭,家人相亲相爱。她有两个姐妹,瑞雅和玛莎,还有一个兄弟,纳胡姆,他们都留在立陶宛生活,金达则在一九二四年选择来到法国求学并且和一名俄罗斯裔医生结了婚。我母亲爱莲娜我舅舅皮埃尔先后出生了。关于莎乐美,只留下来一张照片。
照片上有日期,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还有这个名字,阿帕纳缪,用蓝色墨水写在了照片右上方。我很久都以为阿帕纳缪是摄影师的名字,但后来却发现帕纳缪是科夫诺一座郊区,“这是立陶宛最美的地方之一,尼曼河在这里绕了个圈”,那儿也有第四集中营,是科夫诺犹太隔离区几个行刑地之一。
画面上是一对夫妇和一个小女孩儿。莎乐美两三岁大,金色的头发剪得齐齐的,留着偏分,脸上露出调皮的微笑。她穿着白色绣花的裙子。莎乐美不是骑在她父亲的脖子上,而是完全坐在了他的右肩上。父亲用右手托着她,左手紧紧搂着他的妻子瑞雅,我外祖母金达的姐妹。瑞雅举起左手来握住她丈夫的手。她穿着一件白色西装裙还有一件印花的衬衫,眼中透着活力,也梳着偏分,棕色的头发拢到了后面,腕上戴了一只金色手镯表。男人叫马克斯·伯恩斯坦。他已经有点秃顶,裤子的皮带显得过紧了,身上穿着衬衫打着领带。他们一家人在一幢木屋前拍照,隐约能看见一扇窗户,带花边的窗帘,铺着瓦片的屋顶还有一个街道号,19。
这是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一个立陶宛犹太家庭拍下的其乐融融的照片。这张照片我从没在外祖母家见到过。
金达独自凝视着他的姐姐、外甥女还有姐夫,不敢把照片给任何人看。直到一九九。年,她才将照片拿出来,她带着它去了耶路撒冷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为了填写战争中消失的三十一位家庭近亲的见证卡。在她外甥女的卡片上,她附了这张照片。这张她从未给她女儿看过的照片。母亲爱莲娜跟我提过莎乐美,“她连一张照片也没留下。”在母亲和外祖母之间,围绕不在人世的莎乐美保持着一层缄默。既没有图片为证,也没有语言交流。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