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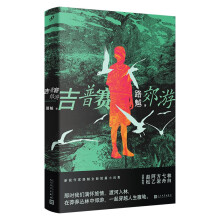







★刘一达“京味儿”小说语言的第四代传人
★京味儿小说语言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
★《人虫儿》《北京爷》被列为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主题百部推荐图书
★北京市“京味语言进校园工程”推荐书目
本系列丛书立足当下、面对现实,将北京四十年来的社会变革、市井变迁透过其创作的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和精彩传奇的故事表达了出来。书中不但有丰富的人物形象,更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也为北京传统文化提供了*威、丰富的文学史料,带给老一代美好的回忆,新一代年轻人阅读北京、感受北京的文学读本。北京老百姓生活的巨大变化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北京人民爱国爱家的情怀,都通过本系列丛书中一个个典型的文学形象、一篇篇精彩的文学故事,生动地展现出来。
“虫儿”这个词来自北京方言,对一般读者而言也许有点陌生。老北京把“精通某行业务或知道某行内情的人”称为“虫儿”。相对应每个行业,都有不同的“虫儿”。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大潮涌动下,北京城里出现了一批“虫儿”:倒腾房子的“房虫儿”;有前门胡同里长大,靠“玩”古玩收藏发了家的“古玩虫儿”;还有当过“板爷儿”、卖过糖葫芦,最终当上董事长的“买卖虫儿”。除了这些“腕儿”级别的“大虫儿”,还有今天我们依然熟悉的“票虫儿”“网虫儿”这些“小虫儿”。
作者刘一达是时代敏感的观察者和提问者。在他笔下,各行业的“虫儿”栩栩如生。通过他的采访、他的文字,忠实记录了那个重要的时代转折点上,富有时代气息的百态人生。
为时代留影,为小人物立传,是为《人虫儿》。
第三章“瓦片虫儿”寻访记
中国的“高老头”
孙博文老爷子透着邪性。
每天,他例行公事一样,出入官园的鸟市,有时也到西直门的热带鱼市溜达一圈儿。玩鸟,他并不在行,手里拎着的那个鸟笼里,一只“百灵”,半死不活,押出的音儿,都是“脏口儿”。懂眼的人说,这只鸟,五块钱也没人要。玩鱼?他连“银龙”与“带鱼”,恐怕也分不清。那他玩什么?八成只有他自己“门儿清”。
七十三岁了,正是“坎年”。他幽灵一般在人们的眼前打晃儿。
躬腰塌背,牙掉得没剩几颗,腮已然嘬了进去,眼神也不济,眼眶子上总趴着点眼屎。那身“行头”,让人瞅着寒酸,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还缺两个扣子,菜汤儿留下的痕迹总是在显眼的位置。嘴上叼着不带嘴的劣质烟卷——“香山”或是“大婴孩”。这种烟连捡烂纸的老头儿都不会抽它。
穷。这老爷子真够可怜的!这副尊容够十五个人看半个月的。
十个人有九个人瞅见他,会这样说。
他听了很得意,仿佛他在街面上踽踽独行,专为了听这一耳朵。
他的得意是含而不露的。喜怒哀乐,在他的脸上都品不出来。一年到头,他似乎总是一种表情——苦相儿。
他很少与人交谈,嘴上像贴着封条,透出迟缓与木讷。他似乎没有什么亲近的人,尽管他的人缘儿是那么地说不上来是好是坏。他好像并不在乎街坊四邻的眉眼高低。
老年人的孤僻和苦寂是很可怕的,即使最不合群的老人,总希望找个能说话的“伴儿”。他却不然,总是独往独来,形单影只,似乎没有体己的人。
他的穷困潦倒的形象也许连街头捡破烂的老头儿都不如,虽说,谁瞅见他,都会很自然地与捡破烂的联系起来。
他真是穷到这份儿上了吗?
只有知根知底儿的人才会知道,孙老爷子是个“瓦片虫儿”,他“吃”瓦片儿已吃出个百万富翁来。而这老爷子是根“油条”,他在跟人们玩“花屁股”——有意遮人耳目,掩饰他家财万贯的真相。
若不是记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抠他的底牌,绝对想象不到他是“大款族”里的一员。
他到底存了多少钱?至今是个难以破译的谜。
不过有一点,他最后向我透露:不少于五十万!
妈爷子!五十万!赶上五百人的工厂一年的产值。
当然,按他的人头儿,他说出的这个数是打了马虎眼的。
他的话,有一半是掺了水,另一半是“油”。
“京油子”。一点不假,孙老头儿是个典型。
他有俩儿俩女,都已成家,另起炉灶。按道理说,他这么大岁数,身边该留住一个,儿子或是女儿。但是,他一个也不要。据说,并不是儿女不守孝道,而是他坚决不要。
“想沾我的光,姥姥!”
别看他是“闷坛子”,说出话来能把人噎一溜跟头。
“骨肉亲情呢?您难道不讲这个?您可是个老派人呀!”
有一次,我斗胆相问。
“骨肉亲情?扯臊!儿女就那么回事。来了,没别的,眼睛盯着我的钱袋呢,嘴,一个人就是一张嘴,虎口!我不指望沾他们的光,也甭想。老了,我有钱,这年头,有钱什么也不怕。”
他梗梗着脖子,干瘪的脸涨得通红。
他的儿子叫他“高老头”。这是巴尔扎克笔下的一个畸形老吝啬鬼的形象。
我实在佩服孙老头儿子的想像力。
他跟我讲了这样一件事:
孙老头儿七十岁时,四个儿女合计了一下,不管老爷子怎么抠门,也算是“老家儿”,该给他祝寿。自然,为老爷子祝寿,从他身上拔毛是不可能的。于是四个儿女凑了四百块钱,在西四的“同和居”摆了一桌。虽说孙老头儿不掏一个大子儿,但是,他却把儿子为其祝寿当成了向他敲竹杠的机会,死活不去。二儿子舍着脸跟他说,二女儿耐着性儿跟他央告,真是“三顾茅庐”,寿星老儿最后才开了面。
本来,他要走着去,可是从西直门外到西四,七八站路,二女儿让他雇辆“三轮”或打“的”,老爷子不肯花这脚钱,最后是坐公共汽车去的。下了汽车,他见到二女儿,二话不说,拿出汽车票说:“谁让你们请我来的。这两毛钱车票你得给我报销。”他二女儿一听,差点没背过气去。
两毛钱!孙老头儿的账居然算得这么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