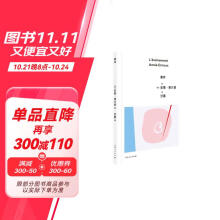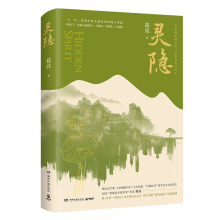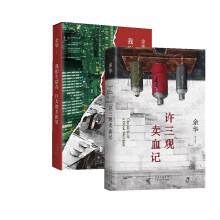《角儿》:
“几点了,天咋这么亮?”母亲醒了,她嘀嘀咕咕,一边穿衣服,一边撩开窗帘向外看,外面下雪了。母亲迅速下了炕,打开房门走到院子里,见地上已经飘落了一层雪花。母亲走到房后,在一间低矮的煤棚子里取了劈柴和煤块,她进了屋把炉子点燃。
屋子里有了一点热乎气,父亲随后也起来了,他轻轻地拍了拍睡在旁边的儿子,说:“江子,起床吧,快五点了!”
睡梦中的常江子一骨碌从热被窝里爬起来,还没睁开眼睛就迅速地穿衣服,起床后与父亲一起收拾行李,准备出发。
雪花渐渐变大,且纷纷扬扬地飘洒着,精灵般的雪花越飘越勇猛。一会儿的工夫,天空、大地、房屋、街道连成了白茫茫的一片。整个世界白莹莹的,闪着柔光,散发着恬静。小镇还在一片懵懂与宁静中,父亲推着一辆红旗牌自行车,后车座上带着一捆行李,送常江子去汽车站。
天气刺骨般寒冷,父亲手上戴的是一副白色的线手套,早己被冷风穿透。母亲用围巾把头部裹得严严实实,呼出来的气体很快变成白霜,与雪花一样的白霜挂在她的眉毛上。常江子走在父亲和母亲中间,他穿着一件黄色军大衣,手里拎着一个旧提包,三个人一起来到了长途汽车站。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长途汽车条件非常差,车里没有暖气,也没有行李厢,旅客们的行李就放在汽车的顶部,放上去用绳子捆住。父亲和常江子把行李从自行车上拿下来,举着递给站在车顶上的乘务员,乘务员把这最后一捆行李放好,用绳子绕了几圈,捆得结结实实。父亲踮起脚,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围着汽车看了一圈,直到他相信那行李不会在半路上掉下来为止。这一切安顿好之后,父亲对常江子说:“上车吧!”
常江子冻得嘴唇发紫,他说:“爸、妈,你们快回去吧,天挺冷的。”
母亲脸上的表情已经冻僵,可她的目光闪闪烁烁,泪珠儿在眼睛里含着。母亲担心地说:“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赶上个大雪天。我看这雪会越下越大,路会很滑的,你路上要多加小心啊!”
“放心吧,妈。你们快回吧!”
父亲的心情同母亲一样,可父亲表面上就像一座平静的山峰,他催促着常江子说:“快上车吧,司机师傅等着开车呢。”
常江子迅速上了车。汽车缓缓起动,雪花更加肆无忌惮。常江子坐在靠窗的位置,他回过头向父亲和母亲招手时,汽车的玻璃窗上面已经挂满了白霜。他急切地用嘴上的热气哈玻璃窗,双手迅速地去擦玻璃窗上那层冰霜,刚刚擦出一小块透明的地方,汽车已经驶出了车站。
汽车开得很慢,雪天,车里更加寒冷。坐在车上的旅客有的抄着手,有的跺着脚,人人都抱着膀儿,把脑袋缩进脖子里取暖。常江子似乎没那么冷,只有他一个人笔直地坐着,他心里发热,一直处于亢奋状态,他用右手摸着自己胸脯,感觉那里是最温暖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小布兜,是临行前母亲在他的棉袄里边用一块旧布缝的,兜里装了二十元,还有一张很重要的字条,那张字条上边写着辽北省玉琼市样板戏学习班的地址,常江子到了玉琼市后,需要按照这张字条上面写的地址寻找自己的工作单位。
此时,他的脑海中浮现出许许多多画面,一幕一幕地回想,事情的前前后后似乎都发生在这样的大雪天里。
“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齐步走……”常江子喊着口令,操场上那白茫茫的一片雪地,忽然间布满了凌乱的脚印。
那是刚刚复课的校园,学校半军事化管理,体育课就是军训课,班级不叫班级,叫几连几排,班长不叫班长,叫排长,排长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喊口令,口令一定要喊得干脆响亮,像军人一样。
常江子不仅口令喊得好,响亮,有激情,人长得也精神、帅气,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他喊口令时,动作做得十分规范标准,就好像是从部队里训练出来的一样。他的~举一动都很有感染力,在他的口令声中,队伍走得整整齐齐。因此,班集体经常受到学校表扬。无论上课间操还是体育课,他带领的一连一排都是学校里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后半节课,体育老师发慈悲了,说:“同学们辛苦了,下面的时间你们可以自由活动了。”
“噢!噢……自由活动了!”同学们兴奋地喊着,个个像放飞了的小鸟。男生们不约而同地蹲在地上攥雪球,他们准备打一场雪仗。虽然个个脸冻得红扑扑的,头顶上还冒着热气,玩儿起来却不感觉冷。女生们则不然,只有几个人留下来和男生们一起打雪仗,其余的全都怕冷,跑回了教室。
“江子,江子!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常江子的雪球还没投出去,忽然听到一个很亲切的声音在喊他,去回过头望去,是陈大中老师在办公室门前向他招手。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