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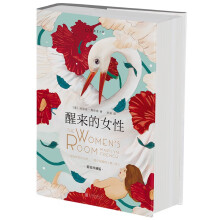









在1980年代的蔷薇街,时间像门前流水,依约而行,人们悠然地一边吃早餐,一边八卦街坊邻里间永远共享的秘闻,一天由此开始。国营照相馆的摄影师顾大宏单干后,全然不像是一个做生意奔前途的样子,在晨光中,他捕捉情人关文梨一低头的剪影。女儿顾小妍开始了青春期的绽放,身上带着不敢直视的光亮也带着摄人心魄的美。儿子歪头用自己寡言的视角,注视着父亲隐秘的情感,也仰视着姐姐骄纵的魅影,同时学会了惦念自己喜欢的女生。
一场舞会的对决,一场少年的冲突,虽然蔷薇街的栀子花如常开放,一个跳舞时代无可奈何地终结成了过去。在花街往事中,路内用文字带领我们徜徉了一下那个让人眷恋的1980 年代。
屠户虽然被他小舅子揍了一顿但他们根本拦不住他,除非那两个猪倌天天在家里监视他,这不现实,猪会没人管。等他们回去之后,屠户又开始跳舞。他在文化宫俱乐部颜面丢尽,不好意思再去,后来到哪儿鬼混,我爸爸也不知道。
屠户一辈子没穿过什么好衣服,即使在他热恋的时候。其实他比我爸爸有钱,但他不在乎外表,觉得把钱花在这方面是穷威风,宁愿攒下来买电视机和四喇叭,那才是享受。到了一九八五年他的人生观算是彻底颠覆了,以前的衣服,只是一些劳动布的外套,上班的时候加一条围裙,下班把围裙摘了。人们对他的认识,就是穿围裙和不穿围裙的,现在他以西装示人,穿起了皮鞋,最可怕的是他给自己配了副平光眼镜,一下子文静了。
他也戴领带。学着电影里的国民党和资本家,让他老婆给他打领带,他老婆织毛衣还可以,打领带完全外行,不是歪了就是松了,让我爸爸去诊断,我爸爸一看这他娘打的是红领巾的结啊,赶紧纠正了。屠户的第二天又是红领巾出来了。我爸爸就告诉他,实在不行就别解开那个结了,像上吊一样把自己脑袋钻进去,再收紧,也是可以的。后面那些年,屠户的老婆给他晾晒领带,都是一圈一圈的挂在竹竿上,很像公共汽车上的拉环。
到了冬天,他又闹着做了一件黑大衣。人家说他脖子太短,黑大衣兜在肩膀上,活像是偷来的,必须有一条围巾来衬托出他是有脖子的。于是他命令老婆给他织了一条晴纶围巾,米色的,在脖子上绕几圈,晚上骑车出去跳舞不那么冷,起静电什么的就无所谓了。然后,他又去旧货市场给自己搞了一顶同文帽,都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的产品,看起来很像《上海滩》里的许文强,或是许文强杀死的某个流氓头子。这身打扮让人们觉得街面上凭空多出了一个人,鬼头鬼脑骚唧唧,来自民国,去往未来。
冬天的某个黄昏他来找顾大宏,非常神秘,像十八岁欲火难熬的小王八蛋那样把我爸爸勾到一边,说:“老顾,带你去个好地方。”
“去干吗?”
“当然是跳舞。”
天快黑了,顾大宏在吃饭,他不想出去。屠户说:“真的很好玩,比你去过的所有场子都好玩。”顾大宏嗤之以鼻,像屠户这样的人,他还能去什么像样的场子?屠户在他耳边低语:“家里办的舞会。”
“黑灯舞。”顾大宏放下筷子。
屠户不知道黑灯舞的意思,他对这种切口还不熟,但他领会了意思,说:“是啊是啊,黑灯舞。没跳过吧?”。我爸爸再次嗤之以鼻,心想老子就是在黑灯下面学会跳舞的,当年张道轩师傅家。他扒了几口饭,起身换衣服,并叮嘱我们:“帮我洗碗,早点睡觉。”
小妍说:“你不回来了?”
我爸爸说:“当然要回来,就是晚一点而已。”
小妍说:“你们是去做地下党吧?”
这两个人骑着自行车穿过城区,经过城南大桥,护城河以外很远的地方,都快到郊县了。那儿有一个正在挖土造房子的新村,立着几栋黑漆漆的楼。夜里停工了,很多毛竹棚子里透出灯光,像是个宿营地。屠户说:“小心别摔了。”两个人推着自行车进了新村。
那种舞会才是公安局真正会查抄的,城里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轮着严打可以把所有参与者都抓进去判刑。可是它真的很刺激,在一九八五年,所有一本正经和没正经的人都想进去看一看,到底什么才叫黑灯舞。
屠户带着顾大宏走进一栋房子,整个楼道里都黑着,看来还没人住进来。可是楼下又停着好些自行车,有男式车,也有女式车,大致说明了状况。到了二楼听见隐隐的萨克斯风,一户人家窗口透出幽微的灯光,屠户敲门,里面有人问:“谁?”屠户说:“我方明。”门一开,音乐豁然清晰,里面的烟味也跟着飘了出来。
这是一套两居室,只经过简单的装修,头上是灯泡,脚下是刷过清漆的水泥地坪,没有窗帘,贴了报纸遮光。客厅里一张宽大的人造革三人沙发,翻下来就可以当床,一个女的斜坐在沙发上,一个男的坐在扶手上,其余人等在屋子里跳舞。音乐来自一台电唱机,黑胶木唱片转啊转的。那种舞,人们都知道,叫做贴面舞,但它也并非纯正的黑灯舞,纯正的黑灯舞是干脆把灯全部关掉,在黑暗中上下其手,即使是方屠户也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吧?
贴面舞是这样的:男性的双手搭在女性的腰里,女性的双手挂在男性的肩膀上。从人体力学的角度来说,它方便于双方贴近,造成了从脖子到腰臀共同扭动的局面。当时为了避嫌,公开的交谊舞要求双方必须保持着比正常标准更远的距离,乳房和胸膛之间得有一肘远,导致舞姿变形,很像是个四条腿的动物在转圈。贴面舞则告诉大家,舞,不是这么跳的。贴得越近,跳得越性感。我爸爸在窗户底下还看到了另一种舞:男的从背后抱住了一个女的,两人跟随着音乐若有若无地扭一下,那个女的,她对着窗户在抽烟。
顾大宏当时的反应大概就像我猛然踏进了四化时代[1],看到了气垫飞车在天上跑来跑去的场面。他是舞界名人,假装很镇定,忽然肩膀上被人拍了一下:“顾老师也来啦。”回头一看是个女的,苏华照相馆某一期的舞蹈学员,他赶紧说:“过来观摩一下。”然后就坐在了沙发上,点了根烟,表示自己不想跳舞。
屠户坐在了扶手上。顾大宏问他:“这是谁家?”屠户说:“我来给你介绍介绍。”他走进里屋,带出来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文质彬彬,非常潇洒,左手拄着一根拐杖。屠户说:“这是文化馆的岑老师。”岑老师说:“顾老师,久仰久仰。”我爸爸肃然起敬,掐了香烟和他握了握手。
这位岑老师在戴城声名赫赫,他是某个资本家的儿子,家里报得出名字的亲戚全都在海外,剩下他一个不知道怎么回事,没出去,文革还被人打断了腿,从此成了个瘸子。多年来他一直被监管着,八〇年以后日子稍微好过了些,在文化馆搞搞美术创作,客串到电台主持古典音乐的节目。以前他住在城里,那间破屋子里有诸多胶木唱片,每个星期天的下午都散发出咖啡的香味——他可能是戴城唯一煮咖啡的人。
岑老师说:“这是我新分配的房子。常来玩,过阵子我会把唱片都搬过来。”
顾大宏说:“我师父张道轩活着的时候经常提起令尊。”
岑老师苦笑道:“不堪回首,不堪回首。”
岑老师离开后,顾大宏问屠户:“你来过几次?”屠户说这是第二次。顾大宏追问:“一个人来的?”屠户嗤之以鼻:“当然不是,我的女人等会儿就来了。”顾大宏一时无语,倒想看看屠户能找到什么样的舞搭子。过了会儿,外面真的来了几个女的,其中一个胖嘟嘟的圆脸盘,一双杏核眼,年纪不过二十多。这回屠户没再介绍,他很快搂住这姑娘在屋子里跳起了贴面舞。顾大宏惊讶地发现,老方的舞技有了长足的进步,尽管他身材矮胖,腿脚局促,但他的舞步中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像一块刚从猪猡身上割下来的新鲜的肉,温热,柔软,真实。从姑娘的表情来看,很享受,很快乐,那就意味着屠户靠他自身的魅力终于把到了姑娘。我爸爸看着看着,忽然觉得头皮一凛,这姑娘和红霞小姨是同一种长相,在暗促促的灯光下她们甚至可以说非常相似。
回家的路上,顾大宏欲言又止:“那个和你跳舞的女人……”
屠户说:“她叫小霞。”
我爸爸叹了口气:“好吧,小霞。没什么,以后来跳舞小心点,派出所会查的。”
“在这种荒郊野外?”
顾大宏想说,派出所的警察又不是摆地摊的,难道专门在灯红酒绿的市中心活动?这种问题和屠户讨论起来会没完没了,变成车轱辘话,他就没说什么。屠户倒发问了:“为什么你现在不和关文梨一起玩了?”
顾大宏说:“我就算和关文梨一起玩,也不犯法啊。”
屠户说:“那可不一定,关文梨的男人还关在牢里呢,说是离婚了,不过你可别忘了,他是一拳打瞎别人眼睛的老流氓。”顾大宏听了就赶紧说:“我和关文梨没什么,她已经不理我了。”屠户说:“我知道你心里在嘲笑我,可是你他娘的有什么资格嘲笑我呢?”
第二次再去岑老师家,顾大宏遇到了关文梨。她坐在三人沙发的一侧,没有跳舞,只是用皮靴轻轻踩着音乐节拍。顾大宏走过去和她打了个招呼,她站起来,微笑着说:“你怎么能说我不理你了呢?”他知道屠户又在传话,只能说:“我请你跳个舞吧。”关文梨诡异地一笑,眼睛向右后方斜过去,我爸爸看到一个穿猎装的男人,长得既瘦且硬,脸上的棱角像假山一样,一口烟牙,混身上下散发着烟气仿佛他是从大烟缸里酿出来的。顾大宏很知趣地退到一边。
那个男人,他绰号叫作“老克拉”,在戴城的跳舞界,他比顾大宏更有名气,也更有号召力,如果说顾大宏是一根过滤嘴的万宝路,那么老克拉就是雪茄,前者是大众情人,后者才是真正的实力派。虽然他品行不端,爱搞女人,但这正印证了他的厉害,而我爸爸,他只是习惯于搞搞暧昧,属于很软的货色。
老克拉连看都没看顾大宏。我爸爸的好处就是,如果你不想看见他,他就会让你看不见。两个人相安无事,很不像是戴城舞界的两大巨头,既无碰撞,也不切磋。我爸爸站了一会儿打算走,这时屠户又来了。
屠户才不管谁是硬货谁是软货,他拽了关文梨就跳舞,虽然不是贴面舞,也够可以的了。屠户有恃无恐,谁让关文梨当年在他家里蹭看电视的呢,顺便也嘲笑一下顾大宏。可是屠户忘记了舞场上的规矩,如果女方有固定的舞伴,他必须和那个人打个招呼,以征得同意。舞跳到一半,老克拉站起来整了整猎装,走了。关文梨强忍着陪屠户跳到一曲终了,也走了。剩下我爸爸在一边抽烟,对屠户说:“你闯祸了,一点规矩都不懂,你得罪老克拉了。”
屠户说:“我怎么不懂规矩?我故意的。小气死了,一天到晚假装自己是扑克牌里面的大怪。”
顾大宏说你等着瞧吧,老克拉五十年代就在舞场上玩,可阴了,连张道轩师傅都着过他的道。屠户无所谓,这个仇就这么结下了。老克拉和关文梨再也没有来过。
5
一九八六年的春天,岑老师家里办了好几次黑灯舞会,它很像是私人派对,渐渐有了点名气。新村里陆续有人搬进来,人多眼杂,顾大宏曾经提醒岑老师小心点,但他不以为意。岑老师是个很骄傲的人,也很浪漫,否则不会被人打断腿。
五月里顾大宏和方屠户又去了岑老师家。那阵子屠户玩得特别疯,除了黑灯舞以外,还迷恋上了迪斯科,经常去青年宫门口晃悠,那儿有个露天的迪斯科舞场,不幸总是被人当作社会流氓赶出来。那时小霞已经消失了,换成了小红,我爸爸心想下次就该是小李了,这样屠户就能把“李红霞”三个字给拼凑出来。
屠户和小红跳舞,顾大宏坐了一会儿,那天人特别多,他觉得有点闹,决定先走。虚虚实实地打了一圈招呼,看屠户情在浓处也就没叫他,独自走下楼,刚到门口就听见下面杂沓的脚步,有人压低了声音说:“二楼,就在二楼!”
我爸爸是何等聪明的人,一九六七年能从保派的埋伏圈里救出我妈,顺带稍上超重的胖姑。听这动静返身就往楼上跑,楼下的人健步如飞,他根本来不及去岑老师家里报信,顺势刺溜一下跑了上去,直到顶楼。那里漆黑一片,他点了根火柴,看了看周围的情况,一梯四户,大门全都敞开着,里面是脏了吧唧不明所以的毛坯房。我爸爸多了个心眼,没钻进去,要是那天他进去了,其下场和其他人大概也差不多。他在墙角找到一把竹梯,架起来,从天花板上的一个方孔里钻了上去,爬到楼顶上,顺便把梯子也收了上去。
楼下一阵啰唣,来的是派出所和联防队,他们迅速控制了场面,两人一组,全部带走。忽然听见一串脚步声,有人跑了上来,站在方孔下面纳闷:“哎?梯子呢?”跟着联防队就追上来了,一阵暴打以及惨叫,把人拽了下去。我爸爸心想,真是不好意思,你自认倒霉吧。这时楼下好像又有人逃跑,警察大喊:“站住!开枪啦!”我爸爸心想,要命,抓跳舞还带枪吗。等了很久,到底也没有听见枪响。
等到这些声音都消失时,已经是半夜了。四下里全无声音,他松了口气,站在楼顶上眺望远处,一些汽车和摩托车亮着红色的尾灯离去,戴城城区寥落的灯光,一轮明月挂在天上,脚下的水泥屋顶泛着银灰色的寒光。他找了一张草包铺在地上,坐下来抽烟。当晚天气不错,有点冷。我爸爸看看手表,已经十一点多,但他不敢贸然下去,要是逮住了很有可能被送去游街。他决定,干脆天亮了再说。
我爸爸在屋顶上待了一夜。楼顶的风肆无忌惮吹在身上,他在泛着寒光的屋顶上独自跳了一圈华尔兹,停下来抽根烟,又跳了个探戈。这么消磨着,后来撑不住了,躺在草包上睡了一会儿,醒来时发现天还没亮,冷得像是被抛在了月球上。看看手表,原来只是眯着了十来分钟。
熬到天色微亮,他实在不行了,快冻死了,就把梯子放下去,钻回方孔。经过岑老师家时看见门口贴着个封条,隔着窗户朝里探望,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清,想必是被抄干净了。他蹑手蹑脚下楼,在楼下开了自行车锁,忽然看见屠户从工棚里钻出他那肥嘟嘟的脑袋。
“老顾,你没有被抓走!”
顾大宏说:“你也没有?”
屠户说:“我跳楼了,我从阳台上跳了下去,他们没发现。”
“那你还不回家?”
屠户大声呻吟道:“我的腿崴了,我是爬进工棚的。”与此同时,工棚里的建筑工人也起床了,有人说:“要不是我们藏着你,你就等着被送去劳动教养吧。”方屠户说:“你倒不说我给了你们一人十块钱。”建筑工人说:“操,警察走了你倒是嘴硬了,昨天晚上躲被子里哭呢。”
屠户没法骑车了,只能坐在自行车的书包架上,由我爸爸骑车,两个人灰头土脸回家。屠户说:“这下岑老师惨了。小红也不知道怎么样了。”顾大宏说:“你就别惦记别人了,腿没摔断都算你运气。嗯,岑老师惨了。”屠户说:“这种事情肯定是有人告密,我怀疑是老克拉干的。”顾大宏说:“你又没证据。”屠户再次感叹:“岑老师惨喽。”
我爸爸艰难地骑着车子,由于吃相太难看,他没有取道城南大桥回家,而是从城外绕着,沿着公路经过面粉厂,再从城西大桥折返回蔷薇街。这条路他们很少来,以为还像从前一样人烟稀少,这才发现它热闹了很多,好几个新村的公房都造了起来,上早班的人络绎不绝。面粉厂还在。走着走着,屠户忽然说:“你还记得一九六七年吗,那次你骑着黄鱼车把我拉回红旗桥。”
顾大宏说:“那次累死我了,车上还有李红霞和大耳朵。”
屠户沉默了一会儿,说:“前几天小妍对我说,我还在想着李红霞。这帮小孩怎么什么事情都知道?”
顾大宏说:“小妍也不小了,十七岁了。”
屠户说:“我他娘的反思了一下,我可能真的还在想着她。我他娘的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很怨恨我?”
顾大宏说:“我们怨恨你什么呢?”
屠户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要是不结婚,她就不会去昆明相亲,不相亲她就不会翻车死掉。大耳朵不会死,李苏华也不会死。你们都这么想吧?这么多年没说出来而已。”
顾大宏说:“我没这么想过。”
屠户说:“我就是这么想的。”
顾大宏说:“那你也不用说出来,自己想着,就可以了。”
他们回到蔷薇街,一个脚崴了,一个吓破了胆,总算消停了一阵子。没多久传来消息,岑老师判了,特大流氓活动组织者,他经历了审讯、开除、公判、游街、登报等等一系列的标准化流程。公安部发出通知,整顿舞场,清除精神污染,一时风紧,以为从此又要回到旧时代。不料到了一九八七年,一纸令下,开放营业性舞厅,跳舞成了一门合法的娱乐,没多久就连未成年人在舞场里混迹都没人管了,又过了一阵子,连舞女也有了。于是岑老师就成为戴城最后一个因舞获罪的人。事情就像坐了过山车一样惊险刺激,难以预料。那个时候,人们都明白一个道理:任何时代都有它的牺牲品,上个月的牺牲品可能是羊,下个月就成了鸡,谁搞得清呢?
在风声鹤唳的最后一段时光里,一种马海毛的棒针衫悄悄流行起来,它宽大而艳丽,使女性的上半身陷于一片柔光,像海藻或是蒲公英般漂浮着。在舞厅里,女人穿着这种衣服使禁令难以实施,因为它很大,又缺乏明显的边际线,跳舞时根本搞不清乳房和胸膛之间的实际距离。你说贴着了,里面的真材实料还差着一尺多远呢,你说没贴着,这衣服中间的空隙只需稍稍一挺胸就能在暗中消弭。这种衣服其实很有外国鸡的风范,只是人们不知道,以为穿高开衩旗袍的才是鸡。后来时代变幻,人们玩起了国粹穿上了旗袍,又觉得穿马海毛的才是鸡。再后来,旗袍和马海毛都穿在了鸡的身上。总之是他娘的一笔糊涂账。
[1] 四化时代,1980年代中国提出过一个口号,到2000年中国要进入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简称四个现代化、实现四化。这个口号非常普及,不过到2000年的时候已经没人提这件事了。
目录 · · · · · ·
第一部 当年情
第二部 相册
第三部 跳舞时代
第四部 疯人之家
第五部 胖姑结婚
第六部 痴儿
· · · · · · (更多)
第一部 当年情
第二部 相册
第三部 跳舞时代
第四部 疯人之家
第五部 胖姑结婚
第六部 痴儿
第七部 日晕月晕
第八部 光明
路内的小说是一代人的精神镜像。他笔下的青春,不仅是年华,也是灿烂的心事,不仅常常受伤,也饱含生命的觉悟。
——第14届华语传媒大奖授奖辞
路内明了自己是在写一些恒久动人的东西,它们和泪水有关,但他并不会直接去书写泪水,而是侧身去描摹那些被泪水烧灼过的青草和花朵。
——评论家 张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