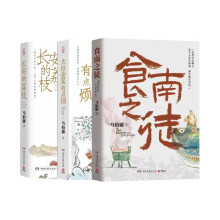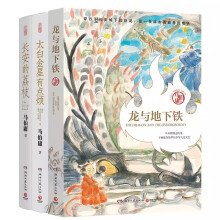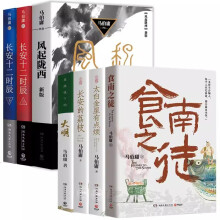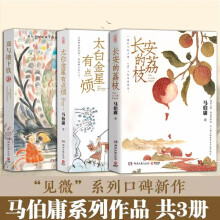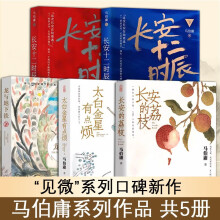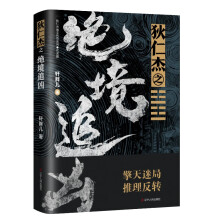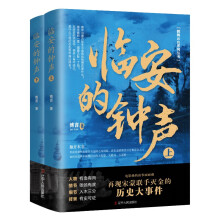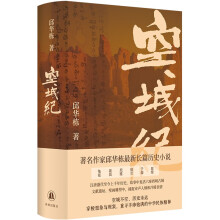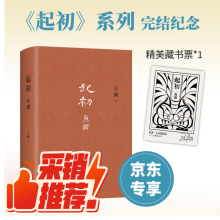第一章 初见
山苍苍,
水泱泱,
渔家小女织网忙。
杼梭梭,
线长长,
织出罟网送情郎。
虾慌慌,
鱼惶惶,
网中有我莫乱闯。
对于住在松花江边的人们来说,这首歌谣不知唱湿了多少渔女的眸,也不知唱欢了多少青年的心。
但虞葭很长时间都不懂歌的真义,每当她在村里姐姐们织网的间隙要问个清楚时,都会招来一阵嬉笑。有姐姐告诉她说:“等我们美丽无双的葭妹妹长大就明白喽!”
可是,长大是多么遥远的事呢,难道像姐姐们那样整天在江边盼归吗?盼回了自然欢喜,盼不回的就只能独自望着江水流泪?小虞葭偷偷地想,长大了就会有那样一位可以盼归的人吗?
那一年,虞葭十岁,还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但与村里其他同龄的姑娘不同的是,她本不属于这里,她不记得自己是几岁时跟随被流放的父亲到了这里,只记得小时候在江南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那时的她和众多的大家闺秀一样,稍大一点儿就会读书、识字、学画、抚琴……十六岁以后或许还会遇到谁家的公子,成就一段美好的姻缘……
然而,随着父亲因一桩公案莫名受到牵连被流放后,她的人生就被彻底改变了,随之改变的,还有她的未来。
流放到位于松花江边的大乌喇虞村那年,她才三岁。父亲或许是为了融入当地族群,抑或是为了忘却一段记忆吧,而改姓虞,她的名字也就变成了虞葭。按照父亲的说法,希望她像刚刚露出新芽的芦苇那样在岸边无忧无虑地成长,忘却世间繁华,独享乡野清雅。
然而,乡野没有清雅,有的只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循环往复,有的只是在松花江里捕鱼的艰辛和那满身的鱼腥。父亲时常告诫她,她不属于这里,并总是在劳作之余教她琴棋书画。父亲说,总有一天会有机会让她重新过上那本属于她的生活。不管是江南小镇,或是州府城郭,哪里都行,就是不能去京华。
小虞葭始终不知道父亲所说的京华是哪里,更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去那里,问过多次后,父亲只是说:“让你学习这些只为了将来能找个好人家。”
“像织网的姐姐们希望的那样吗?”那时的她天真地问。
父亲拍着她的头,无限感伤地说:“这村里没有人可以娶我的宝贝虞葭。”
稍大一点儿后,再提及此事,虞葭说:“我哪儿也不去,我要向村里的姐姐们那样学会织网,也要学会驾舟,学会捕鱼,将来就在这里陪父亲终老一生。”
就这样,小虞葭在父亲身边快乐地成长。月光下,她捧书读史,为书中才子佳人的故事所感动;白日里,也可与小姐妹们一起去河边看织女结网,倾听她们婉转的渔曲;在父亲的船头,看父亲挥舞魁梧的臂膀撒网捕鱼,幻想着将来自己那个他的模样;有时,也和姐妹们在河边浅水处嬉戏打闹,仿佛已经完全融入她们之中,自己也是一个渔家女;夜晚独处时,她也会轻抚父亲的琴,弹那渐渐长大的少女心事……
短短几年,虞葭已经出落成了大姑娘,而她,也学会了那首渔女谣,只不过除了轻柔曼妙的曲调外,她偷偷地借《诗经》和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中的诗句给改了词:
瞻波松江,维水泱泱,
谦谦君子,来自何方。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京华何在,可有情殇。
蒹葭玉立,娇容如霜,
橹桨渖渖,宛在水中央。
让虞葭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填词的这首渔女曲在冥冥之中预示了自己的未来。
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初夏的一天,十六岁的虞葭像往常一样做好了晚饭,平静安闲地立在窗前望着远处的江水,等待捕鱼的父亲晚归。
看着父亲和几个乡邻回来了,她高兴地跑出去帮父亲把肩上的鱼篓卸下,又忙着把做好的饭菜端到桌上。她明显发觉今日父亲有些异样,平日里父亲每次回来都要问一问她今天学了什么,看了什么书,可今天父亲似乎忘记了,难道是有什么心事?
“父亲,是今天江上不顺?”她为父亲盛好了饭,又斟了一杯酒放在桌上。
父亲只是轻轻地“哦”了一声,没有多说什么就开始吃饭。
见父亲眉头紧锁,她就不再问了,默默地吃饭,然后默默地收拾,又默默地帮父亲整理渔具。
“葭儿,不用整理了,夜深了,你睡吧!”身后传来父亲苍老的声音。
虞葭回过头,惊异地看着脸上写满沧桑的父亲,问道:“明天不用出船吗?”
父亲走到窗前,望着一轮皎洁的明月,许久才喃喃自吟:
昨日江山昨日花,
江水奔流忘还家。
威仪浩荡今所至,
蒿柳怎敢吐枝丫。
虞葭一听,顿时吓了一跳,父亲随口吟出的这首诗可是犯了大忌,这要是让官府的人听到那可是要杀头的呀!
“父亲——”她轻唤了一声。
父亲回过头来,慈爱地看着她,轻声道:“睡吧。明天为父早些出船,恐怕最近一段时间入不了江了……”说完,他回了房间,只留下呆呆发愣的虞葭。
听父亲的话里似要发生什么事,她再回想刚才父亲的那首诗,“威仪浩荡今所至”,是有什么人要来吗?或许,明天应该去江边一观。她这样想。
月留江水江自流,
一缕清辉万千愁。
可有君子同瞻玉,
细说京华在哪州。
睡不着的虞葭独自望月,受父亲感染,也吟了一首。此时的她,却想起父亲所提的京华之事。
常年在父亲的诗书中徜徉的她,越发对外界好奇起来,除了这个熟悉的虞村,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书中那些男男女女的故事真的那么美好吗?父亲所说的京华应该是皇权之地吧,也会有这般的圆月吗?思忖间,少女心事尽显。
可是,她的思绪还是被打断了。
随着外面一阵脚步声,她看见院子里突然亮了起来,似乎多了许多灯笼火把,紧接着,就传来一阵紧似一阵的敲门声。
她披了一件衣服,惊诧间,看见父亲前去开门,门闩卸下,未及开门,就从外面冲进几个人来,竟是身穿官衣的兵勇。
“将军有令,流放之奴即刻收监!收拾收拾跟我们走吧!”其中一名兵勇说道。
虞葭被吓了一跳,但她看见父亲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既没有争论也没有询问,只是淡然说道:“请几位官爷外面稍候,容我穿件衣服!”
几名兵勇出去后,虞葭扑到父亲身前:“父亲!他们这是要……”
父亲轻抚了一下她的头,长叹一声道:“为父很快就会回来,你自己在家要照顾好自己,切记,万不可去江边凑热闹!切记!”说完,父亲回屋穿了件外套就出了门,跟那几名兵勇走了。
倚在门口,虞葭望着远处那一队明灭的灯火,不禁悲从中来。想自己和父亲两人相依为命,不曾分离过,可今晚官府究竟为了何事要带走父亲收监呢?
一夜未眠。虞葭只盼快些天明,也好到邻家问个明白,或是到江边探个究竟。可是,父亲临走时为什么说不让自己去江边呢?自己从小就在江边玩耍,父亲从来不曾阻止过,此次又是为何?
好不容易盼到了天亮,虞葭早早地起来,穿好了衣服就准备到邻家问一问。可等她到了邻家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应,她不禁狐疑起来,平日里自己的好姐妹清莲都是起得很早的呀,今天怎么会不在家呢?
她正想转身返回去时,却一眼看见一位大婶行色匆匆的样子,等上前一问才知道,原来村里此时已经没什么人了,大家都跑去了江边,说是要一睹龙颜。
“婶子,江边发生什么事了?”她好奇地问道。
“哎呀,你怎么还不知道呢?去看看就知道了,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呀!”说完,她不等虞葭再问就走远了。
虞葭望了望东方初升的太阳,耳畔似乎听到了江水声,夹杂着还有此起彼伏的赞叹声和隐隐传来的锣鼓声。
此时正值五月,应该不会有什么值得庆祝的节日呀,她疑惑不已。
想起父亲昨晚的话,她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回到家里。她也无心吃什么东西,喝了一杯水后又拿过一本书坐在窗前,准备让自己忘记心中的烦闷,去书里找些许慰藉。但耳边一阵紧似一阵的锣鼓声搅得她心神不宁。江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父亲不让去是不是因为自己是女儿身?想到这儿,她放下书,到父亲屋里找出几件父亲的衣服来穿在身上,那些衣服虽然大了些,但腰带一束也还过得去。她又找出一条布巾包裹在头上,拿过铜镜一照,自己也不禁哑然失笑,这哪里还有女孩儿家的影子,活脱脱就是一位俊美的渔家青年嘛。
她装扮好后就急匆匆地出了门,朝江边走去。
此时的松花江边人声鼎沸,沿江两岸旌旗招展、锣鼓喧天。众多兵勇三步一人手持枪戟面向江心而立,在他们身后,众多围观的百姓都伸着脖子望向江心。
虞葭不敢往前面挤,以她弱小的娇躯也挤不进去,她就找了个高处远远地望向江面。映入她眼帘的,是一列浩浩荡荡的船队,且极尽奢华,前面三五官船过后是艘巨大的龙舟,上插五行彩旗,龙舟上也有身穿铠甲的兵勇肃立,船头旗罗伞盖之下立着一人,只见他身披大氅,上绣龙纹,正在指着岸边景致和身边的两个人不时地说着什么。因为离得远,虞葭看不清他们的容貌,但从这阵势上看,她明白了,莫非是皇家船队?
船队行得近了,她又看去,这回看清了,但目光所及之处却并不是身披大氅那人,而是在那人身边所站之人。就见那是位青年男子,身披铠甲,腰挎佩剑,眉宇间英气逼人却隐隐透着一种忧郁。
虞葭多看了那人几眼,心想,此人想必是侍卫吧。
此时,官船和龙舟都停了下来,岸上的兵勇围出一条通道来,船上的人开始下船。
虞葭见好多百姓都站在兵勇围成的人墙两侧,她犹豫了一下也朝那边挤了过去。还没走出多远呢,突然,就见周围的百姓都纷纷跪了下来,还以山呼海啸般的声音高呼着:“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她被这阵势吓了一跳,站在人群中不知所措,只是惊恐地望向越走越近的那些身着华服的人,还有那些旗罗伞盖。在中间最大的那顶伞盖下,她看见了刚才龙舟上身披龙氅之人,虽相貌年轻,但气宇轩昂,绝非凡夫俗子。伞盖之侧,正是那名貌似潘安的侍卫,在中间那人半步之后紧紧跟随,目光还巡视着围观的百姓。
正在这时,就听有人大喝一声:“你好大的胆子!见了圣驾竟敢不跪!”
还没等虞葭反应过来呢,肩膀就挨了一鞭子,打得她差点儿掉下泪来。她回头一看,见一名兵勇怒目而视,手里扬着鞭子作势还要打。
“你怎敢随便打人!”她揉着肩膀狠狠地瞪着那人。
“不想活了是吧?”那兵勇扬起鞭子就要打。
虞葭吓得闭上了眼睛,可她等了半天也没见鞭子落在自己身上,悄悄睁开眼睛一看,却见那名侍卫正抓着兵勇的手,兵勇吓得浑身筛糠一般。
就听那侍卫低声冷冷地喝道:“圣驾面前你怎敢造次!还不退下!”
兵勇缩着脖子退了下去。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