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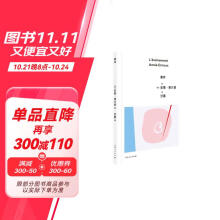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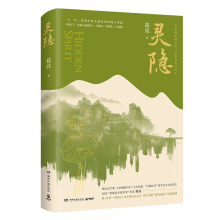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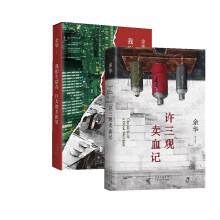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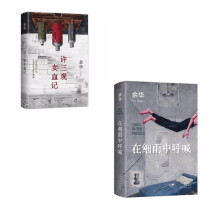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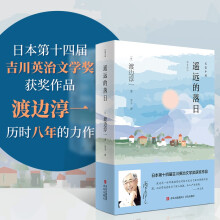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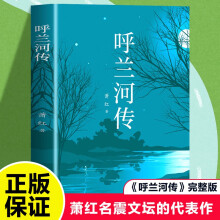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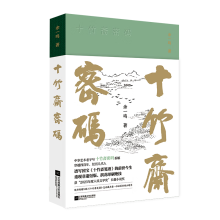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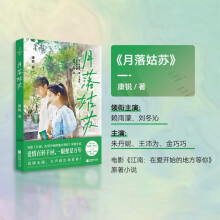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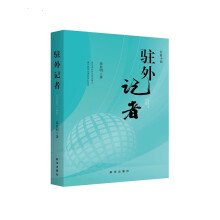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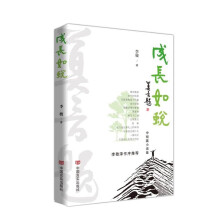
70后作家徐则臣的代表性力作。将城市边缘人纳入文学视野,探讨城市与人的关系。
《天上人间》 :一群外来者为了理想和生活,从四面八方闯入当下的北京。他们年轻或者不年轻,一例具有深入生活前线的勇气和毅力,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建立自己与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机遇与前途遍地的淘金之所的隐秘的联系,在物质生活上有所收获,在精神理想上有所寄托;但事实并不能如预期所料,京城米贵,居之不易,而他们从事的又是与这个开放的法制城市格格不入的行当,制造假证,他们是一群伪证制造者。他们饱受法律和正义的追逐,要躲着阳光在街角和阴影里出没。当他们侧着身子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里艰难地行走,突然抬头看天,他们将何去何从……
《天上人间》是将这些城市边缘人纳入当代文学视野的长篇小说,真实地呈现了伪证制造者们在北京的希望与绝望、确信与疑难、卑微与正大、阳光与阴影,小说描绘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这也是一部在“新北京”的背景下,着力探讨城市与人的关系的小说,它与我们的时代息息相关……
引子
小峰在蓝旗营的一家饭馆里等我,透过雾气蒙蒙的玻璃我看见他坐在窗户边上脖子乱转,可能等急了。饭馆里暖气很足,进了门我有点鼻塞,空气突然就变黏稠了。外面可是很冷,我把风衣搭到椅背上,拿餐巾纸擦了擦玻璃,马路上的行人努力把脖子往锁骨里顿。两重天啊,我跟小峰说,我那小屋里暖气打死也上不去,害得我不停地跺脚,棉脱鞋都跺坏了。
“那还每周请我吃饭。”小峰说,“都穷成这样了。”
“一顿饭还是请得起的,你哥没到那份儿上。”我对走过来的服务员先伸一个指头,再伸两个指头。服务员明白,一个指头是一个大份芷江鸭,两个指头是两瓶啤酒和两碗米饭。脸早混熟了,我和小峰在这里吃了一年,基本上每周一次。这家馆子里的芷江鸭做得地道,一年了我们俩都没吃厌。
“最后一次,这是。”吃完了小峰抹抹嘴,“弄得我每到周末就想着这事。吃饭吃饭,跟尽义务似的。”
“啥意思?”
“没必要老请我吃饭。”
这小子,我请客还成他负担了。他是我弟弟,我姑妈的儿子,现在清华念大二,80后,挺懂事的孩子偶尔也会说昏话,我不能跟他计较。咱们是好哥俩。
“我是说,既花钱又耽误你的事。我知道你忙。”
我一下子没回过神来。我明白这小子没说出的意思是,每个周末都雷打不动地下馆子,他要为这顿饭不得不重新规划周末,其实也挺耽误他的事的。可是,我别的也做不了什么啊。姑父进去的时候跟我说,小峰就交给你了。姑妈也说,在北京,小峰就你一个亲人了。当时听得我鼻子发酸。什么忙都帮不上的时候,只能请吃饭。现在我不吭声,点上根烟。
“我想去看看我爸。”小峰说。
“没什么好看的。”
“我看看自己的爹也不行?”
“在里面挺好的,吃穿不愁。”我说。这也是姑父对我说的。
两年多了,每次我去那里他都这么说。我好像应该相信他在里面过得不错,人明显胖了。当然我也不是经常去看他,没时间,跑一趟大老远的。没空你就别来了,常替我看看小峰就行。姑父语重心长,简直像托孤。他再两年就能出来了。我跟小峰说:“再忍忍,等出来了,你可以一天到晚盯着看。”
“哥,带我去,就一次。”他伸直右手食指对我隆重地许诺。就一次。
一次也不行。姑父说了,不能让小峰去,耽误他念书;还有,让同学和学校知道,影响小峰前途,找工作都是个污点。有个蹲班房的爹总归不是件脸上有光的事。
这个理由小峰十分地看不上。什么年代了,个人信息里又不要写家庭成分;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我说是这么个理,但理是理事归事,天桥底下那个缩脖子的你看见没?就那个,穿灰棉袄的,对,向行人打手势的那个。
“我爸就那样?”
“差不多吧。不过你爸长得帅,收拾得光鲜利索,所以求人的时候也经常像在下命令。”
姑父是个办假证的,被警察逮了个正着,人赃俱获,而且场面还不太好看。那时候他刚跟一个叫路玉离的女人从床上下来,被褥乱糟糟一团。路玉离是他在北京的情人,也干这行。姑父之前进去过,二进宫判得就有点狠,还好再两年就出来了。如果能找个机会戴罪立功,或者表现好点,没准还可以提前几天。即使一天天熬到头,也指日可待。起码姑父是这么想的,那里面的生活其实不错,就是想睡个懒觉有点麻烦,一大早得起来出操,干活。天桥底下的灰棉袄又向一个行人做手势,被那人挡了回去。我又拿张餐巾纸把玻璃擦亮堂些,让小峰看清楚灰棉袄是如何难堪地站在冷风里。
“我爸他——”
小峰说了句半截子话是正确的,他从没见过他爸向陌生人兜售假证。灰棉袄做得很不好。即使杀人犯看见他爹如此狼狈也会心里难受的。当然我姑父不至于这样,在做假证的这个行当里他绝对是个体面人,哪怕穷得连碗泡面都买不起,走在路上他也要把墨镜戴上,小肚子挺起来,脚步杠杠的。人活着不容易,尤其在北京这地方,妈的,得让自己像个人样。姑父刚来北京时就这么经常教育我,那会儿我还在念大学。但我不能让小峰怀疑他爸也是灰棉袄这样,事实上很多办假证的站在路边都会有此遭遇。不想搞个假证的人多半都怕他们,见着了要像避瘟神一样躲开。
所以我模棱两可地跟小峰说:“知道你爸的苦心了吧。”
这话激起他强烈的求知欲和辩驳欲。“这么苦,为什么他还耗在这里?多少年了。”小峰连带对我都鄙夷起来了,我也在这里,东奔西跑,采访,码字,大冬天住一间暖气总也上不去的小屋。“中国这么大,哪里黄土不埋人?”
如果让姑父来回答,他可能会说:“北京的黄土跟别的地方不同嘛。”
按照我的修辞习惯,我也可能这么说。只是说完了我会心里没底,原因在于,不同究竟在哪里我也说不好。刚来北京时我可能会跟你扳着指头数出个一二三来,但现在,生活日久我越发不知道北京的不同在哪儿了。现在的北京跟十几年前的北京肯定是不同了,它的不同不是因为它复杂了,而是因为它复杂得你已经难以描述清楚了。
“很多同学都想毕业后留在北京,神经病!”小峰用筷子拨溜剩下的鸭头,可能觉得没事干,夹起来开始啃,“念完书我就走,随便去个地方也比这里好。宁当鸡头不做凤尾。”
念书的时候我也想过去外地做鸡头,京城米贵,为了找个坑要花那么多心思,没劲;可最后还是留下来了,削尖脑袋跑细了腿要找个坑把自己栽进去。栽进去的时候还想着鸡头和凤尾的辩证关系么?好像没有,就是留下来而已。好像也没有因为北京机会多或者别的某某原因,接着想象要做一个鸭头、鹅头或者猪头之类。就是想把自己在这里栽下来,生根发芽,长出枝叶来。
目 录
引子 1
上部:啊,北京 7
下部:我们在北京相遇 101
旁部:天上人间 183
题解:伪证制造者 277
后记 332
再版后记 336
北大当然能够培养出优秀的青年作家,比如徐则臣,他在当下的青年作家中独树一帜,他对北京的书写,眼光独到且有自己的发现。
——曹文轩
徐则臣笔下的京漂或伪证制造者是一种边缘人,或者说是一种流动的底层、非法的底层、另类的底层。与“打工者”相似,他们也是从农村或小城镇来到北京的,但他们并不从事一种固定、安稳的工作,而是流浪在这个城市中,以制造或贩卖假证为业,走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缘,也走在“正常”与非正常生活的边缘。这样的职业决定了他们必然走在一条冒险的路上,并充满了内在的矛盾,他们与这个城市的各个阶层都有接触,熟悉其中的一切但又无法融入其中,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偶然性,收入不固定,情感不稳定,并时常会遭遇到警察或同行的暴力,以及欺骗、侮辱或竞争。这样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小社会,可以说是徐则臣的独特发现,他丰富了我们对都市尤其是都市底层的认识。
——李云雷
身份焦虑,同一性危机,偏狭可怕的力量,无意义的时间洪流……徐则臣展览的其实正是你、我、他本人,正是我们的日常。
——樊国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