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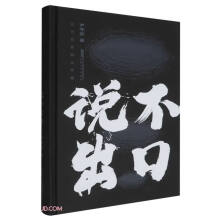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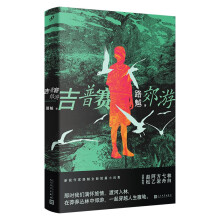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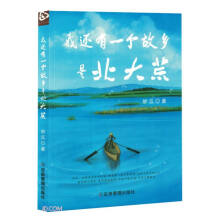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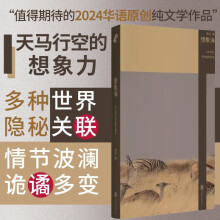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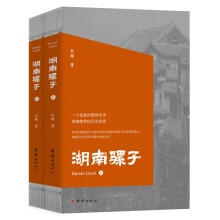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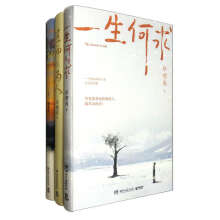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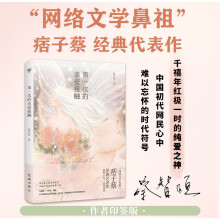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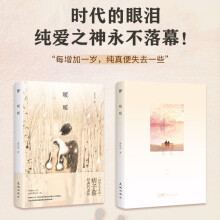
所有的母亲都是从“女儿”这个身份转变而来的,但每一位母亲和每一位女儿之间的关系却各有各的不同。苏黎红是个优雅了一辈子的女人,虽年过六十,身材却依旧窈窕,喜欢读《红楼梦》,爱听王菲、周杰伦的歌,“生病”时常做“西施捧心”状,这样的苏黎红注定不同于一般的母亲。
她是朱小燕的母亲,却始终偏爱着小儿子朱鸿鹄。“小燕”和“鸿鹄”在她心中的分量似乎单从名字就能窥见一二。作为长女,朱小燕从小骄傲而独立,她一直想在母亲面前证明自己,却一次又一次地败给现实。她心中的隐痛和埋怨,ZUI终化成了“苏黎红小姐”这个对母亲陌生而缺乏温度的称呼。这种情感难以诉说,却又无比真实。
也许“有些东西,ZUI初的拥有,就是永远的拥有;ZUI初的匮乏,就是永远的匮乏……一个人只有ZUI初学会了和母亲相处,才能学会和世界相处。”
阿袁用深刻的笔触刺中了这种中国式家庭关系的核心——它是拼命抑制的情感,是欲说还休的交流,是吵吵闹闹的相爱,是亲亲热热的怨恨,ZUI终,又全都化作了无法逃避的责任。
正如阿袁在创作谈中写到的那样:
“谨以此作,献给中国的女儿。”
我们也把这本《苏黎红小姐》献给全天下所有的朱小燕们。
《苏黎红小姐》是“布老虎中篇小说”中的一种,共收录阿袁的《苏黎红小姐》和《左右流之》两个中篇小说。
《苏黎红小姐》:美丽的苏黎红小姐是“我”妈,她特别优雅,也有些矫情,于是“我”总以DI三人称的方式称呼她。由于没有遗传她的优秀基因,“我”自幼就没有弟弟朱鸿鹄受宠。也因对弟弟的偏爱,苏黎红多次插手他的婚姻生活,导致弟弟前两次婚姻破裂,母子间也渐渐产生了嫌隙。弟弟再婚后,尽管苏黎红与父亲老朱倾其所有帮助他买房,但也未能回到往日的亲密关系。面对逐渐老去的苏黎红,“我”与她的感情也在不断变化。她和儿媳米宝的矛盾注定了她不会去弟弟那里养老,而“我”也正好到了买房的决断时刻,是购买只适合二人世界的“布鲁塞尔”,还是选择能容纳父母居住的“闲情偶寄”,“我”和苏黎红的感情似乎也要在这里做个决断。
《左右流之》:住在八号楼里的一群大学青年老师喜欢聚集在苏小粤宿舍闲聊,她文雅、孤傲而又博学多识,谈的多是阳春白雪的话题。但温和、世俗,有着浓重烟火气的周荇搬来后,老师们被周荇对生活的热情所感染,闲聊的中心渐渐迁移到她的房间。家庭妇女一样的周荇因为她的烟火气吸引了学校里的单身男老师。一边是“心高气傲又志存高远”的大才子陈亥,一边是“长得且黑且矮”的电工小余,周荇却鬼使神差地选择了后者……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周荇似乎都能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正是在她左右流之、爰得我所的自如中,映照出知识分子看似正常生活中的窘迫和僵化。
阿袁的小说既有张爱玲式的华美,又有钱钟书式的幽默,读后让人感到惊艳,只觉满口余香。她总能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引入千丝万缕的文化印迹,诗词歌赋信手拈来,字里行间弥漫着雅致的意境。即使是写家长里短这类小事,也能将阳春白雪的书斋生活与烟火气十足的市井生活打通。但她的雅又是很接地气的,极少引用生僻的诗句,而是在大家熟悉的诗词里进行巧妙地化用,点石成金,有化腐朽为神奇之感。
电话响的时候,我正在巴黎一栋公寓的走廊里。走廊里弥漫着某种气味,什么气味呢?阳台上的花香?阳台的黑木箱里有一种我不认识的花,粉紫色,看上去有点儿像我们中国的绣球花,也有点儿像锦葵。但那种气味却不像花朵的。或许是刚刚从我身边经过的男人身上的香水味?巴黎男人是搽香水的,和女人一样,所以整个城市都香喷喷的,像闺阁。但那种气味要说也不像香水味——结合了男人体味的香水味,是一种生命的味道,虽然有一种可疑的不洁,但蓬勃茂盛。可弥漫在走廊里的气味,却是腐朽和衰败的,像大夏天厨房里放了几天的不新鲜的瓜果蔬菜。
到底是什么呢?有警察急急忙忙地往公寓某间房间走。原来是一个老妇人死在公寓里了。说是被谋杀的。
我惊恐不安地想上前看看,就在这时,电话响了。
公寓消失了,奇怪的气味也消失了,眼前黑漆漆一片,什么也没有。我恍惚了半分钟,才反应过来:刚才的事情,不过是电影里的场景。
睡前我和孟周看了迈克尔·哈内克的《爱》。
床头的夜光闹钟,指向早晨四点半。
电话是苏黎红打来的,这个时候,除了苏黎红,没有人会打我家的电话。
我心口痛,燕子。
嗯。
你知道米宝那个狐狸精对我们做什么了吗?
米宝那个狐狸精是朱鸿鹄的老婆,我的弟媳。而“我们”,是苏黎红和老朱,苏黎红是我的妈,老朱是我的爸。
她做什么了?
她给你爸打电话,说小鲤想吃爷爷的南瓜粥了。你也知道你爸这个人,贱得很,一听孙子要吃他的南瓜粥,高兴得手舞足蹈,哼着黄梅调就去了,“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他就会这两句,连后面的“从今再不受那奴役苦”都哼不出来,还好意思总哼。一路上,他就哼哼那么两句,你说烦不烦?
就因为这个,你大清早给我打电话?
岂止。米宝竟然还对你爸说,他一个人去就可以了。做点儿南瓜粥,不用兴师动众的。她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不让我去他们家?
不让你去他们家?怎么会?
怎么不会?她这可不是DI一次了。上次小鲤生病,她也这么说了——说希望爸爸过去帮忙照顾小鲤,不用辛苦妈妈了。还说,他们家房子小,妈妈过去也不好住。燕子,你听听,你听听,这女人歹毒不歹毒?我和你爸,形影不离大半辈子,老了老了,难道还要分居吗?
我忍不住想笑。米宝这个女人,也太会算计了。竟然想“买珠还椟”。她不知道,在我们家,这珠椟是不能分的。
朱鸿鹄呢?朱鸿鹄怎么说?
他能怎么说?他现在是米宝养的鹦鹉了。米宝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也不知道这女人给他下了什么蛊,把他变得言听计从的。
米宝还会蛊术呀?我讽刺苏黎红。
苏黎红不理我,自己说自己的。这也是苏黎红的风格。
还有更气人的呢!我们去了才发现,原来不是小鲤想吃南瓜粥,而是老狐狸想吃呢。老狐狸染风寒了。你说米宝过分不过分?过分不过分?她妈想吃南瓜粥,她竟然打电话让你爸过去给她煮,这事她也做得出来?我一气之下,要拂袖而去,可老朱还不肯走呢,说既来之,则安之。亲家母想吃南瓜粥,那就煮呗,也挺好。他这个人,燕子你是知道的,就是没有自尊心,没有原则性。我坚持让朱鸿鹄送我们回来了。我要让米宝拎拎清楚,那只老狐狸算什么东西?凭什么老朱要为她煮南瓜粥?可回来后老朱还在那儿叽叽歪歪的,他什么意思?难不成他想自个儿留那儿煮粥给老狐狸精吃,然后让我在家和小区里的樟树一样喝西北风?燕子你说说,你说说,老朱是不是脑子出毛病了?
苏黎红挂电话的时候,已经早晨六点了。早晨六点是苏黎红开始做瑜伽的时间,苏黎红是很注意保持身材的,她六十多了,身材从后面看,还和少妇一样,是十分窈窕的。当然,从前面看也很窈窕,只不过不是少妇的窈窕,而是老妇的窈窕了。但苏黎红从来不承认自己是老妇,为了和小区的那些老妇划清界限,她基本不参加小区老妇们的活动。小区里的老妇们喜欢打门球,苏黎红鄙夷地说,有什么意思呢?一群老人,围着一个破球,你拨拉过来我拨拉过去,慢腾腾的,老牛拉破车一样。小区里的老妇们在有太阳的日子里喜欢坐在树荫下支张桌子打麻将,苏黎红鄙夷地说,有什么意思呢?几个老人,团团坐了,摸几十张小塑料块儿,眼神还不好,一个个的,都戴了老花镜,盲人摸象一样。小区里的老妇们在春夏晚饭后,会在小区花坛那儿跳扇子舞,老朱让苏黎红也去,这运动多好,既可以活络筋骨,又可以消食,还可以听音乐。苏黎红嗤之以鼻。那也叫音乐?老妇们跳扇子舞的音乐反反复复就那几首,一首《还珠格格》里的主题曲《你是风儿我是沙》,“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还有一首《小苹果》,“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儿,怎么爱你都不嫌多”。这种东西也叫音乐吗?小区里的老妇们经济条件好,跳扇子舞也置了行头的,白色的雪纺衫,白色的雪纺灯笼裤,加上一把木骨大红丝绸扇子,那景致,美得很,尤其在有风的时候,老妇们宽大的灯笼裤,被风吹得飘飘欲举,老朱看了,这时候就会吟哦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老朱傍晚时分也在花坛那儿的,他和隔壁的郝伯伯坐着小马扎在那儿下棋。事实上,小区里的老头儿都在那儿活动,有的下棋,有的练气功,还有的,什么也不做,就坐在那儿聚精会神地看老妇们跳舞。他们正襟危坐的样子,有点儿像在国家大剧院看《天鹅湖》或《睡美人》。老妇们因为有了这些观众,也跳得更加陶醉。她们活泼得很,调皮得很,一把红扇子,在她们手上,被舞得风生水起,时而放到脑后,做反弹琵琶的动作,时而又半遮了脸,做出风情万种的样子。老朱这时候又说了,团扇,团扇,美人病来遮面。老朱退休前是中学语文老师,喜欢用诗词表达美好的印象或情感。苏黎红听了冷笑——老朱说这句话苏黎红其实听不见的,因为她傍晚时从来不去花坛那儿,那是老人扎堆的地方,她不喜欢和老人扎堆,她自个儿绕着湖散步。小区外有一个湖——美其名曰是湖,事实上是一个池塘,不过是个大一点儿的池塘,美一点儿的池塘。池塘周边种了垂柳,还有桃花,是红碧桃,重瓣。春天的时候,花红柳绿,水波荡漾,很诗意的。谈恋爱的年轻人,喜欢坐在这样诗意的环境里,搂搂抱抱,卿卿我我。老朱不去那儿,他看不惯这些行为的,他做了十几年中学的教导主任,对有伤风化的事情,总习惯性地要上前教育教育呢。可人家也不是他们学校的中学生,谁要他这个糟老头儿教育呢?不要的。所以他干脆不去那儿,眼不见,心不烦。他情愿和其他老夫们坐在小区看老妇们跳扇子舞。这个好,他们一个爱看,一个爱被看,两情相悦,有利于养生。但苏黎红觉得他有毛病,不爱看花开,却爱看花败——那些皱巴巴的老妇们,不就是残花败柳吗?不爱看“小桥流水人家”,却爱看“枯藤老树昏鸦”——那些皱巴巴的老妇们,不就是“枯藤老树昏鸦”吗?还“团扇,团扇,美人病来遮面”呢!也是,那些皱巴巴的脸,不遮了怎么能看呢?苏黎红对郝伯伯说。这话有些刻薄了,因为“那些皱巴巴的脸”里有郝伯伯的老婆陈阿姨的脸,但郝伯伯不以为忤,不仅不忤,还高兴得很——他打小报告的目的,不就是要苏黎红恼羞成怒吗。
…………
苏黎红小姐
左右流之
读阿袁的小说,首先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便是她对于小说语言的出色运用……能够活色生香地把男女之间微妙复杂的情感故事,以一种充满书卷气的叙事话语格外传神地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正可以说是阿袁的拿手好戏。
——王春林
阿袁《长门赋》《鱼肠剑》等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丰富驳杂,其小说的精神分析与反讽意味承接了现代写作的传统。
——何向阳
阿袁是大学里的教授,从新世纪之初开始写作并发表小说。她的作品并不很多,但却非常独特,有着张爱玲、钱锺书式的文风,这在当代文坛确实是很罕见的……阿袁的小说就像莲藕,又像拔丝苹果,总能带起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记忆。阿袁的秘诀无他,其实就是个“喻”,她总能把当下的人和事,与诗经,与唐诗宋词,与京剧昆曲打成一片,从而构成了一种极具张力的喻说方式。
——藏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