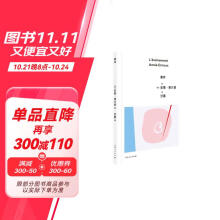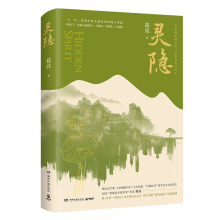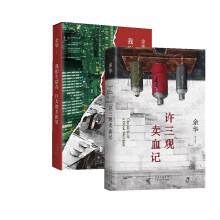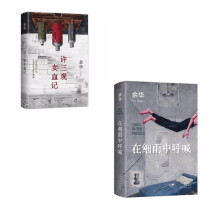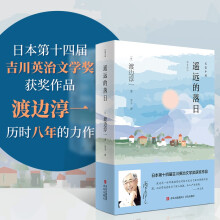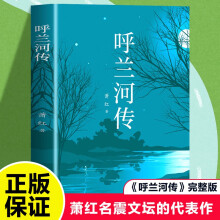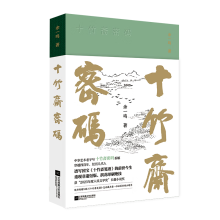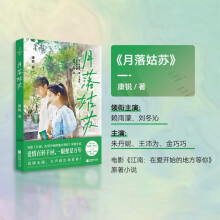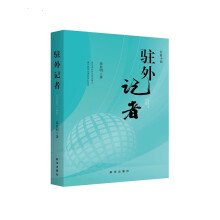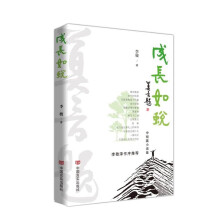《N39°传奇》: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天气很糟。
我刚从学六食堂吃完中午饭回来,心情沉重地走进历史系那幢北洋时代风格的灰色小楼,穿过两侧挂着胡适、顾颉刚、傅斯年、谭其骧、钱穆、夏鼐、徐炳昶、陈垣、邓广铭诸位大师画像的走廊,最终在黄文弼先生的挂像前驻足。
我的硕士论文,《就塔克拉玛干考古发现论述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互动》,目前还是炒冷饭的程度。我的导师羊廉教授当初很委婉地劝过我,不要轻易启动这个课题。可我固执己见,一意孤行。结果就是,除了我,我同届的其他同学都按时毕了业。今年六月之前,能否如期答辩,我眼下一点儿把握都没有。
我自认为有很多的真知灼见,却苦于没有确凿的史料来印证;我又没有亲自前往塔克拉玛干探究考古的能力,一切全是空谈。
十二岁那年,在图书馆首次翻阅到斯文·赫定伟大的旅程——犹如闪电划过黑夜的苍穹,点明了我人生的梦想。
俄国的谢苗诺夫、普尔热瓦尔斯基,瑞典的斯文·赫定、贝格曼,不列颠的奥雷尔·斯坦因,德意志的格伦威德尔、冯·勒柯克,法国的伯希和,美国的亨廷顿,日本的大谷光瑞、橘越超。这些百年前的名字,熟稔到我可以信口呼出。我立志追随这些中亚探险者的足迹,希望能步他们的后尘,在西域文化史上有一番建树。
在大多数世人眼里,塔克拉玛干是一处恐怖凶险之地,只有疯子和亡命徒才会去那种地方。而我,看到一切有关塔克拉玛干的文字图片,都有一种回到故乡的感受。
位于中亚腹地的塔克拉玛干,曾经同时被覆希腊、波斯、印度、中国四大古文明的普照,也是拜火教、佛教、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多个世界性宗教交汇的沃土。论人种变迁的多样性,文化的丰富性,世界上独一无二!
我关心的并不完全是丝绸之路上消失了的古堡、文字、宗教,或者佛寺的文物价值,而是在人类生存、发展史上,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儿,为人类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递进提供了怎样的契机。
可如今,我一事无成,反倒成了一个志大才疏、痴人说梦的典范。我自认为有很多的真知灼见,却苦于没有确凿的史料来印证;我又没有亲往塔克拉玛干探究考古的能力,一切全是空谈。深受我敬仰的黄文弼先生,曾与晚年的斯文赫定有过共事的经历。而与他同样怀有热切梦想的我,却没有任何机会参与到那些磨难当中。
我怀着沮丧的心情回到教研室,打开我的笔记本电脑,一眼瞥见遗忘在课桌上的手机,有三个未接来电显示和一条未阅读短信。
短信上写着:“小A你好,我是郝明。你的老师把你的电话给了我。收到请回复。”
“郝明??”
我一下想起来,我们历史系的马波博士曾经与我断断续续提过这个人的一些情况,说他是个奇人,开过三十多种类型的越野车。有次他跟我说:“小A,你不是天天念叨,想去‘塔克拉玛干’考古吗?如果说世界上有谁能带你进去,还能安全把你给带出来,那也只有他了。”
我立刻把电话回拨过去,那头占线。我刚挂断电话,电话打过来了。
“小A吗?你好,我是郝明。”这是一个富有朝气的声音,听了顿生好感,“今天下午三点,我们开会,确定‘穿塔’行程和参加人员。如果你想加入,我把地址发给你。”
有好一会儿我无法发声,直到那边“喂”了一声。
“您说的‘穿塔’,是穿越新疆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吗?”我小心翼翼地求证。
“就是新疆那个塔漠。”他很肯定地说。
“我想加人!”这四个字我几乎是喊出来的。
“好。成府路到我这儿可不近呢,那你现在就可以出发了。”电话那边说,“你快到亮马桥的时候,提前二十分钟给我个电话,我去接你。”
“我快到了。”我只提前了十分钟给郝明打的电话。
“好,你出来吧。燕莎商场前面有辆紫红色的坦途,打着双闪的,就是我。”
“好。”我回答。
刚从地铁口出来,我就看到街对面停着一辆打着双闪的紫红色的皮卡。
我径直走过去,打开车门,发现这车底盘好高。方向盘后面倚着车门儿坐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五官清秀,白净面孔,吊儿郎当的,左手食指和中指间夹着根烟,伸到车窗外面。他这个样子,很讨一部分小萝莉或者御姐的喜欢——但是对我没用。
这就是刚才和我通话的那个郝明吗——怎么跟电话里的感觉不一样呢?!
那人也斜着眼看了看我:“小A?”
他有点南方口音,咬舌儿,不是郝明!
我松了口气:“是啊。”
那人俯身递过来一只手,要拉我上车。我抓住前把手,自顾自爬上车,系好安全带。
那人不太高兴地把手缩回去,转动钥匙,开车走了。走出去几分钟。上了环路,开车那人问我:“地铁挤不挤啊,小美女。”
“不挤。”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