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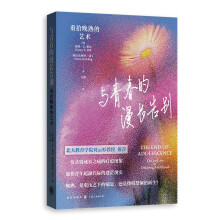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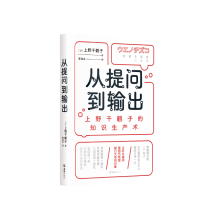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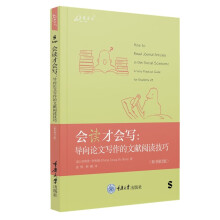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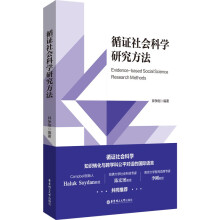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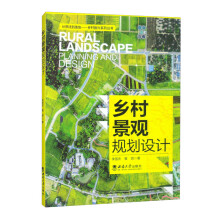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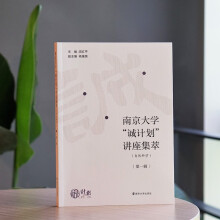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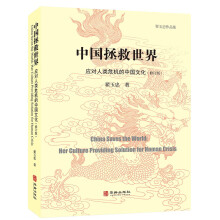

《社会学基本概念(第二版)》对于社会学的入门者以及想为快速变化的世界寻找可靠地图的人来说,这将是不可或缺的阅读材料。
《社会学基本概念(第二版)》介绍了一系列精心挑选的基本概念,其中一些概念过去帮助塑造了社会学,如今也在不断影响其发展,另一些新近出现的概念则反映了最近几十年这个世界的剧烈变化。除了简短的定义外,作者对每个概念都进行了扩展讨论,将其置于历史和理论背景中,探讨了其在使用中的主要含义,介绍了一些相关的批评,并为读者指出了其在当代研究中的演变和理论化。
本书由十个主题组成,通过一些基本概念,如全球化、现代性、可持续发展、消费主义、社会流动、生命历程、身份认同、社会自我、越轨、公民权等,提供了一幅关于社会学的图画。
Social Self
社会自我
定义
指的是在处理他人对自己的各种回应的过程中,一个人形成的自我意识。
起源与历史
通常认为,人类是唯一一种能够认识到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且未来将会死亡的生物。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说明人类具有自我意识。乔治·赫伯特·米德(Mead 1934)关于自我如何形成的思想,是自我形成的研究中最有影响力和原创性的社会学理论之一。他认为,这种社会学视角对于我们了解自我的产生和发展不可或缺。他的思想后来成了社会学符号互动论的基本主张。米德认为,一旦产生,虽然自我基本等同于“思考的能力”(think things through),但它是人类个体从内部生发出来的一个自我,与“灵魂”或“精神”这些类似的概念不一样,社会自我不可能与人类个体相分离。
含义与解读
米德的理论旨在理解和解释,通过模仿和游戏,儿童是如何发展出作为社会化个体(social beings)的自我意识的。我们经常能够观察到,孩子喜欢模仿大人和其他孩子的各种行为,比如组织过家家式的茶会、打理绿植盆栽,或者用玩具吸尘器清洁地毯,这是因为他们看到过大人做类似的事情。这是自我形成过程的开始。当他们着迷于各种游戏时,大约从四五岁开始,自我形成的下一个阶段就启动了。参与游戏意味着,孩子们必须开始考虑不同社会角色的各种特征,而不仅仅是模仿他们所看到的。米德称之为“扮演他人角色”,这要求他们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来看待整个游戏。只有到了这个阶段,社会自我才开始浮现。通过站在他人的立场上,以及就像是“从外部”看待自我,孩子们开始将自己看作一个独立于他人的个体。
将自我分为“主我”(Ⅰ)和“客我”(me)两部分,是米德理论的基础。“主我”,对应的是人类有机体,即那个没有社会化的自我。“客我”,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发展出来的自我,始于上文提及的模仿和游戏。社会“自我”大约从八九岁的时候开始萌芽,彼时,孩子们开始玩组织化程度更高、需要多个玩家彼此配合的游戏。要学会怎么参与有组织的游戏,就不仅要知道游戏的规则,还必须了解他们在其中的位置,以及游戏中其他人扮演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开始学会从外部来看自己,不只是扮演一个简单的独立角色,而是一个“概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这样,个体就能够在相对独立的有机体“主我”和社会化的“客我”之间进行“内部对话”。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发展出自己的自我意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思考”,或者“与自己对话”。有了自我认识作为基石,接下来才能建构更为复杂的个人和社会身份。
批判与讨论
在一部分人看来,米德的自我形成理论把这个过程描述得过于一帆风顺了,但实际上大部分人的成长都充满了矛盾冲突和情感波折,甚至会留下影响一生的精神创伤。在儿童获得 性别认同 的早期社会化过程中,情况尤其如此。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他后来的支持者都认为,相比于米德的理论,对自我形成和性别身份的认知而言,无意识和感觉发挥的作用要大很多。对许多男孩和女孩来讲,割断与父母之间的亲密关系的过程,大多十分痛苦。即使能够相对平稳地度过这个过程,在长大以后与他人建立私人关系时,有些男孩还是会遇到很多困扰。自我的形成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需要对抗无意识层面的各种欲望,米德的理论没有考虑这些内容。还有人指出,米德的理论基本没有关注到父母权力关系失衡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这种权力不平等会造成自我功能紊乱,激发潜在的内部紧张和矛盾。
意义与价值
米德的理论对于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它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系统阐述自我形成过程的社会学理论,强调想要更好地了解自己,我们必须从人类互动的社会过程开始。如此,他告诉我们,自我并不是身体的固有部分,也不是会随着人类大脑的发育而自动形成的。米德告诉我们,对个体自我的研究,离不开对社会的分析,因此社会学的视角就必不可少。
我们或许能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过,亲密关系及其破裂对于我们的自我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有一篇文章(Slotter et al. 2009)考察了恋爱关系破裂对于人们自我概念或“客我”的影响。在稳固的恋爱关系中,人们的自我互相交叉,个体边界变得相对模糊,证据就是日常言语中会更多地使用“我们”(we,our and us),而不是“我”。恋爱关系的破裂通常会给人们带来情绪低落和悲伤,同时也会影响自我的内容和结构,因为人们要重新安排和重塑原有的生活。这项研究显示,在结束一段恋爱关系后,许多人会在主观上对他们的自我产生怀疑,觉得自己的自我变小了。米德和埃利亚斯都认为,实际上,我们的个体体验都在掩饰一个事实,即自我不可避免地是一个社会自我,它一定会受到社会互动和人际关系的影响。
近几十年来,社会学家讨论了许多关乎社会重大变迁的话题,包括全球化、信息科技的传播、大规模移民、旅行、时空压缩、性别关系重建等。这些变化会影响人们对自我的看法,亚当斯(Adams 2007)便将宏观社会变迁的研究和自我认同理论的转变放在一起加以讨论。举例而言,有些理论家就认为,随着阶级认同的淡化,人们的个体自我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明显减弱,导致他们在面对不确定性和社会失范时,变得更加敏感和脆弱。然而,也有人认为,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新的可能性,使得社会自我能够从时代提供的新自由中汲取营养,变得更加灵活多样。亚当斯的研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近些年来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对自我形成过程的影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