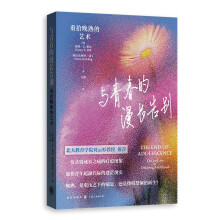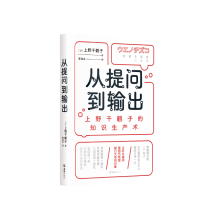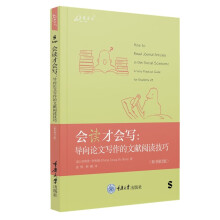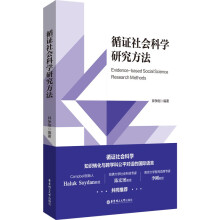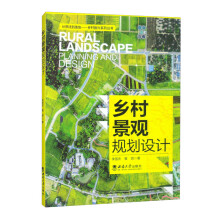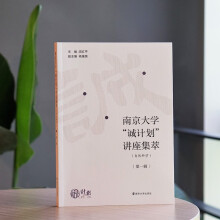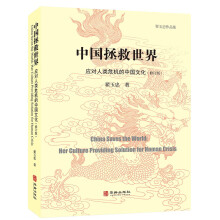角度:为什么我们眼中的世界是如此不同
我在中央车站搭上了一辆出租车赶往一家医院。“你不是病人吧?”司机问道。我得急着赶路,因为我乘坐的这趟从慕尼黑出发的火车晚点到站一个多小时。还没容我回答, 司机就开始讲起自己的遭遇。他的妻子得了重病,是一种癌症,无药可治,已经住院很长时间了。同时,妻子有时也会住在家里,这时就要由他来照料。日子过得很艰难。如果哪一天情况还不错,晚上他就会感到非常幸福。他要做的实在是太多了,像该吃药了、该排便了、该量体温了、该调整疼痛疗法了,等等,无穷无尽。他都快要撑不下去了。这位司机听起来确实很不容易。有时他会觉得这纯属自讨苦吃,有时他则真的不知所措。这就像夫妻俩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 突然有一天妻子对你说:“ 要是一切都结束了那该多幸福呀。”你又该说些什么好呢?
这位司机约有六十五岁,体态臃肿。他讲述着妻子的治疗过程,神情激动,同时也是满腹疑惑,看得出来,他已经讲过这事不止一次了。他似乎忘了我还在车上。突然,他回过神来,好像又想起车上还有乘客,把自己吓了一大跳。如果我不是去看病,而且看起来也不像是在出差,那就只剩下一种解释了。“ 你是什么科医生?”他问道。我强调自己不是医生。不知怎的,听完这话,这位司机松了一口气。“ 哦, 我想也是这样……”
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想。他又接着事无巨细且情绪激动地描绘了一番:没有人肯为他花时间,没有人真正关心他们夫妻俩,人人都在敷衍他们。他们的主治医生老是去找高级医生来帮忙,而那位高级医生每次露面也就短短几分钟,跟着便是对全科医生草草交代一番了事,护士又总是莫名其妙地加班加点。唯一有点空闲的人是医院的牧师,可这是一家新教教会医院,他们夫妻俩又不是这家教会的信徒。
他既找不到能帮他跟医院进行沟通的人,也找不到人去打听他爱人目前的状况。很多说法都是自相矛盾,那帮人根本就没什么才干。听得出来,他已是失望至极。“ 我觉得人还是早点死最好,而且还要死得痛快些,不然自己得不到什么好处,别人也得跟着受累。”接着他又说:“ 这些人在医院里个个无所不能,换个地方也不过如此,死了都一样。”这句话刻骨铭心,透露出一种哲学般的沉重感,一时间我们都有些不寒而栗。随即司机又大笑起来,可能是想稍微缓解一下恐慌情绪吧。
我告诉他我是一名社会学家,正要去拜访这家医院的伦理委员会。这位司机心领神会,话题立刻转向医院里的种种情形。他有一种感觉,借用一句老话来说就是,右手根本不知道左手在做什么。“ 有个医生说,试试让一个医生负责到底如何?他非疯掉不可!这些医生只顾打自己的小算盘,根本不去考虑别人的实际情况。想问问妻子得吃什么药,得去找这个人,想问问接下来该怎么办、在家里又该怎么办,又得去找那个人。这些人各管一摊儿。”
就像是手执一个放大镜,这位司机准确地切中了我这名社会学家的兴趣点。在我看来,医院并不只是一个医疗保健机构,它也是现代生活运转的真实写照:节奏快,层面多, 掌控难,监管压力居高不下,想要破解这些难题却又找不到突破口。这会儿工夫医院到了,我满脑子的思考戛然而止。我付了车费,司机问是否还要回车站,我们约好了时间,到时他再来接我。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