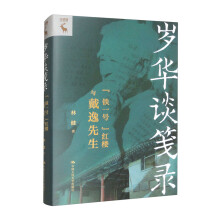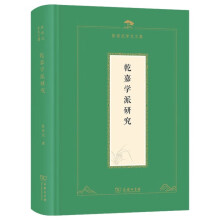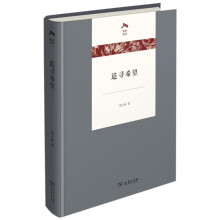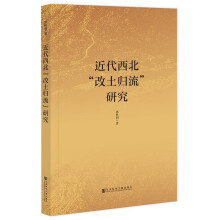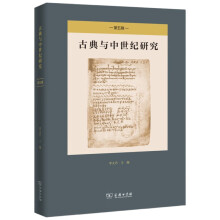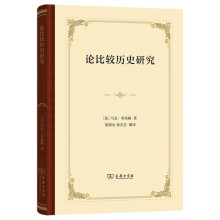下卷
第三章 法国的百年宽容: 反抗
教会将巫师的财产没收之后,就分给了宗教法官和告密者。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执行《教会法》(Canon Law),对巫术的审判就层出不穷,从而给神职人员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凡是世俗法庭宣称对这些审判具有管辖权的地方,这种审判则变得越来越少,并且最终消失了;起码,法国从公元1450年至1550年那一百年间的情况就是如此。
15世纪中叶,法国发出了第一道曙光。高等法院对圣女贞德(Joan of Arc)审判案的调查以及后来的平反,都让人们开始思考起灵魂的交流问题,而不管灵魂是善是恶,同时也开始思考教会法庭所犯的错误。被英国人和巴兹尔总会(Council of Basil)里那些最了不起的神学家定为女巫的贞德,在法国人眼中似乎却是一位圣徒兼女预言家。她的平反,宣布法国开始了一个宽容的时代。巴黎最高法院(Parliament of Paris)同样给所谓的“阿拉斯的韦尔多教派”(Waldenses of Arras)平反了。1489年,巴黎最高法院还像疯了一样,释放了一个被当成巫师而带到那里去受审的人。在查理八世(Charles Ⅷ)、路易十二(Louis Ⅻ)和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Ⅰ)统治时期,这样的人没有一个被定罪。
* * *
西班牙的情况恰好相反,该国在虔诚的伊莎贝拉(1506年)和红衣主教西曼乃斯治下,却开始将女巫处以火刑。1515年,在当时处于一位主教治下的日内瓦,三个月之内竟然烧死了五百人。皇帝查理五世在他制定的德国法律中徒劳地想要夺得管辖权,宣称:“巫术由于会对财物和人员造成损害,故是一个民事问题,而非教会法律的问题。”他剥夺教会没收财产这一权利的措施无果而终,只有叛国罪案件除外。小贵族主教们都通过巫术审判大发横财,因此继续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实施火刑。实际上,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班贝克这个极小的主教辖区里就烧死了六百人,而维尔茨堡主教辖区则烧死了九百人。巫术审判所用的方法极其简单。首先是对证人使用酷刑;通过令人痛苦和令人恐惧的手段,为起诉创造出证人;接下来,利用无微不至的亲切关怀,从被告口中套出某种公开声明,并且不顾业已证明的事实而采信那种声明。例如,有名女巫承认自己在墓地偷走了一名刚死不久的婴儿尸体,好用于配制那种具有巫术的混合物。女巫的丈夫要求法官们前往墓地一趟,因为那个孩子的尸体其实仍然埋在墓中。开棺之后,人们发现孩子好好地躺在棺材里。可是,法官却罔顾自己的亲眼所见,宣称那是一种表象,是魔鬼的障眼手段。相比于事实而言,他更相信那位妻子的供词;于是,她随即就被烧死了。
由于事态在这些可敬的贵族主教当中变得太过出格,因此不久之后,所有皇帝当中最固执己见的斐迪南二世,也就是三十年战争期间在位的那位皇帝,就急于进行干预了;他想往班贝克派驻一个帝国代表,此人应当维护帝国的法律,确保主教法官不会一开始就动用酷刑,进行预先就已定谳、直接判处火刑的审判。
* * *
女巫们很容易因自己的供词而陷入万劫不复之境,有时甚至不用酷刑就会如此。其中的许多人,其实都是疯疯癫癫的。她们会承认自己曾经变成过野兽。意大利的女巫通常都是变成猫;据她们称,她们会从门下的缝隙溜进人家,吸吮孩童身上的鲜血。在森林茂密的地区,在洛林和侏罗山脉上,女巫们则自愿变成狼;而且,如果相信她们所说的话,她们还会说吃掉了路过的人,即便当时并没有人路过。她们都被烧死了。有些姑娘信誓旦旦地说,她们已经把自己交给了魔鬼,可人们最终却发现,她们都还保持着处子之身。她们也被烧死了。其中有几个女巫似乎还极其匆忙,好像希望自己被烧死似的。之所以如此,有时是因为她们陷入了极度的疯狂,有时则是由于她们已经绝望。有位英国妇人被带向火刑柱时,曾如此对民众说道:“不要责怪审判我的法官们。我想要了结自己的性命。我的父母因为害怕而躲着我。我的丈夫休了我。我没法不受羞辱地活下去。我渴望死亡,因此我撒了一个谎。”
第一个公开反对愚蠢的斯普伦格、他那部可怕的手册及其手下的宗教审判员,并且说出宽容之语的,是康斯坦茨的一位律师莫利托(Molitor)。此人说了一句明智之语,说女巫们的供词当不得真,因为那是“说谎之人的父”通过她们的口中说出来的。他嘲笑撒旦的种种奇迹,断言它们全都是幻象。像胡滕和伊拉斯谟这样的弄臣,则用一种间接的方式,通过对多明我会那些白痴进行冷嘲热讽,对宗教裁判所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卡尔丹曾经直截了当地说:“为了攫取没收的财产,同一批人既当原告,又当法官,捏造了一千个故事来当证据。”
宽容大度的传道者查迪龙(Chatillon)的观点,则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观点都相反;此人认为异教徒不该被烧死,只是他对巫师的问题却什么也没说,从而更好地说明了理智之人的态度。最重要的是,阿格里帕、拉维蒂尔(Lavatier)、克莱弗(Clèves)等人的著名医生威尔(Wyer)都曾正确地指出,如果那些可怜的女巫是魔鬼手中的玩物,那么我们必须把责任归咎于魔鬼,而不能归咎于她们;我们必须对她们进行治疗,而不是烧死她们。巴黎的一些医生很快便把这种怀疑态度推进了一步,认为魔鬼附体者和女巫们不过都是骗子而已。这种观点实在是太出格了。其实,绝大多数魔鬼附体者和女巫,都是被一种幻觉摆布的受害者。
亨利二世和普瓦捷的戴安娜两人的黑暗统治终结了这个宽容时代。在戴安娜治下,法国重新开始对异端和巫师处以火刑。另一方面,由于身边都是占星家和魔法师,因此美第奇的凯瑟琳会保护后者。于是,巫师的人数便急剧增加了。据查理九世治下曾经受到审判的巫师特罗伊斯·埃彻勒斯(Trois Echelles)估计,当时这些人有十万之多,并称整个法兰西就是一个女巫之国。
阿格里帕和其他人曾断言,所有的科学知识都囊括于巫术当中。无疑,白魔法当中的确含有科学知识。不过,愚人的恐惧以及他们那种疯狂的愤怒,却让黑白魔法之间没有了多少区别。尽管有威尔这样的人,尽管有那些真正的哲人,但光明与宽容是对黑暗的一种强烈反抗,是在一个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时期出现的。我们的地方法官曾经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表现出了他们自身的开明与公正,如今却投身于西班牙的灵药,有了同盟主义者的愤怒,直到他们逐渐变得比神父更像神父了。在法国对宗教裁判所进行监察的时候,地方法官自己的做法其实与宗教裁判所不相上下,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光是图卢兹高等法院(Parliament of Toulouse),就曾一次性地将四百人处以火刑。想一想当时的恐怖,想一想人们被烧死时腾起的黑烟,想一想刺耳的尖叫与哭号之声当中,夹杂着脂肪可怕地熔化与沸腾的情景吧!自阿比尔教徒被处以火刑以来,还没有出现过这种可恶而令人作呕的景象呢。
但是,这一切对于博登(Bodin)来说,都不值一提;此人是昂热(Angers)的一位律师,是一个强烈反对威尔的人。他一开始就说,欧洲的巫师不计其数,足以与薛西斯的一百八十万大军相提并论。接下来,他又像卡利古拉一样,希望将数量近乎两百万的这些人集中一处,以便他博登可以一次性地将他们定罪和烧死。
* * *
这种新的对抗让形势变得更加糟糕了。法律界的上层人士开始说,由于神父太过经常地与巫师打交道,因此神父不再是可靠的法官。事实上,律师们还一度显得更加可靠。在西班牙,有耶稣会的辩护人德尔·里奥;在洛林地区,有雷米(Remy,1596年);在侏罗山脉地区,有波克(1602年);在安菇,有勒洛耶(Leloyer,1605年)。这些人全都是无与伦比的迫害者,会让托克玛达本人都嫉妒得要命。
在洛林地区,那里似乎出现了一场巫师横行、幻象频出的可怕瘟疫。因为有军队不断经过、有强盗不断侵扰,民众都陷入了绝望当中,只得向魔鬼祈祷。他们都被巫师利用了。如果时任南锡法官一职的雷米的记述可信的话,当时许多的村民因为一方面对巫师心怀惧怕,另一方面又对法官畏惧无比,所以全都陷入了一种双重恐惧当中,全都渴望离开家园,逃往别处。在献给洛林红衣主教的那部作品(1596年)当中,雷米承认,他在十六年的时间里,已经判处了八百名女巫火刑。“我擅长于审判,”他如此说道,“因此光是去年,就有十六人为了不经受我的审判而自尽。”
* * *
神父们感到很惭愧。他们能不能干得比世俗法官更好呢?不能,因为连圣克劳德(Saint Claude)的那些僧侣领主也请了一位世俗法官,即诚实正直的波克,去审判他们手下那些沉迷于巫术的百姓。在侏罗山脉中那个土地贫瘠、点缀着冷杉和稀疏牧场的可怜之地,深陷绝望当中的农奴只能把自己交给魔鬼。他们全都崇拜“黑猫”(Black Cat)。
波克撰写的那本书很有分量。由圣克劳德这位小小法官所著的“宝典”(Golden Book),被高等法院里那些可敬法官们研究,成了他们的指南。事实上,波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律师,行起事来始终一丝不苟。他对这些案件中显示出来的变信弃义之举进行了批评,听不得律师出卖其委托人、法官做出赦免承诺却只是为了确保能够处死被告的做法。他谴责了当时女巫们仍然需要承受的那些靠不住的酷刑。“严刑拷打,”他如此说道,“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种做法绝对不会让她们屈服。”此外,他还非常人道,会在女巫们接受火刑之前就把她们勒死,并且始终如此,只有狼人除外,因为“您必须小心谨慎,把狼人活活烧死才行”。他不相信撒旦会与孩童订立契约:“撒旦极其精明;他完全明白,与不满十四岁的未成年人订立的任何契约,都会因为年龄和适度自由裁量权而无效。”那么,孩子们得救了吗?完全没有;因为此人自相矛盾,并且认为,如果不烧毁一切,甚至是如果不烧到襁褓中的孩童身上,这种有如麻风病一样的瘟疫,就不可能彻底根除。后来要是活着的话,他肯定会走向这种极端。他让乡间变成了一片荒野;世间还从未有过哪位法官,像他这样问心无愧地消灭过民众。
不过,朗克尔在《恶魔的无常》(The Fickleness of Demons)一书中向世俗司法权发出的宏大呼声,却是向波尔多高等法院(Parliament of Bourdeaux)发出的。这位作者既是一个具有某种理智的人,也是波尔多高等法院里的一位律师,带着扬扬得意的神情,描述自己在巴斯克(Basque)乡村与魔鬼斗争的情况;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就在此地消灭了不计其数的女巫,并且更有甚者,他还处死了三位神父。他对位于洛格罗尼奥(Logrono)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怀有同情之心,那里距波尔多不远,就在纳瓦尔(Navarre)与卡斯蒂利亚(Castille)的交界之处;那个宗教裁判所将一桩审判案拖了两年之久,结果却以举行了一场小小的信仰审判(auto-da-fé)、释放了所有女性这种最糟糕的方式而告终。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