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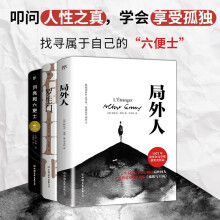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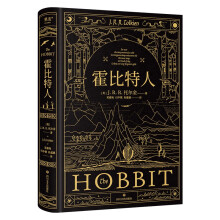




本书精选了莫泊桑*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既有《羊脂球》《项链》《我的叔叔于勒》等脍炙人口的佳作,又有曲折离奇的《怪胎之母》等。莫泊桑擅长从平凡琐屑的事物中截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片断,以小见大地概括出生活的真实。他的小说构思别具匠心,情节跌宕起伏,描写生动细致,刻画人物惟妙惟肖,令人读后回味无穷。
羊脂球
溃退中的残军一连好几天穿城而过。那已经算不得什么军队,倒像是一些散乱的游牧部落。那些人胡子又脏又长,军装破破烂烂,无精打采地向前走着,既不打军旗,也不分团队。看上去所有的人都神情沮丧,疲惫已极,连想一个念头,拿一个主意的力气都没有了,仅仅依着惯性向前移动,一站住就会累得倒下来。人们看到的大多是战时被动员入伍的人;这些与世无争的人,安分守己的有年金收入者,现在被枪支压得腰弯背驼。还有一些是年轻机灵的国民别动队,他们既容易惊恐失措,也容易热情冲动;时刻准备冲锋陷阵,也时刻准备逃之夭夭。其次是夹杂在他们中间的几个穿红色军裤的正规步兵,在一场大战役里伤亡惨重的某支部队的残余。再就是夹杂在这五花八门的步兵中的穿深色军装的炮兵。偶尔还可以看到个把头戴闪亮钢盔的龙骑兵,拖着沉重的脚步,吃力地跟着走路反倒略显轻松的前线步兵。
接着过去的是一队队义勇军,各有其壮烈的称号:“战败复仇队”“墓穴公民队”“出生入死队”等等;他们的神情却更像土匪。
他们的长官有的是昔日的呢绒商或粮食商,有的是从前的油脂商或肥皂商,只因形势的要求才成了军人。他们所以被任命为军官,不是由于金币多,就是由于胡子长。他们浑身佩挂着武器,法兰绒的军装密布着金边和绶带;说起话来声高震耳,总在探讨作战方案,并且自诩岌岌可危的法国全靠他们这些大吹大擂的人的肩膀支撑。不过他们有时却害怕自己手下的士兵,因为这些人原是些打家劫舍之徒,虽然往往出奇地勇猛,但毕竟偷盗成性、放纵不羁。
听说普鲁士人就要进占鲁昂了。
两个月来一直在近郊森林里小心翼翼地侦察敌情,有时开枪射杀己方的哨兵,连一只小兔在荆棘丛中动弹一下便立刻准备战斗的国民自卫军,如今都已逃回各自的家中。他们的武器,他们的制服,不久前还用来吓唬三法里内公路里程碑的所有杀人凶器,也都突然不翼而飞。
最后一批法国士兵终于渡过塞纳河,取道圣瑟威镇和阿沙镇,往奥德麦桥退去。走在末尾的将军已经灰心绝望;他带着一盘散沙似的败兵残卒,也实在难有作为。一个惯于克敌制胜的民族,素有传奇般的勇武,竟然被打得一败涂地。在这样的大溃逃中,将军本人也狼狈不堪;他由两个副官左右陪伴,徒步撤退。
此后,城市便笼罩在深深的宁静和惊慌而又默默等待的气氛里。许多被生意磨尽男子气概的大腹便便的有产者,忧心忡忡地等候着战胜者,一想到敌人会把他们的烤肉钎和切菜刀认作私藏武器就不寒而栗。
生活好像停止了,店铺全都关门停业,街上鸦雀无声。偶尔出现一个居民,也被这沉寂吓坏了,急匆匆贴着墙根溜过。
等待期间的焦虑甚至让人希望敌人索性早点来。
法国军队撤出的第二天下午,不知从哪里钻出的几个枪骑兵,快马流星地穿城驰过。接着,过了不大工夫,就从圣卡特琳山坡上冲下来黑压压一大群人马。与此同时,另外两股入侵者也出现在达内塔尔公路和布瓦吉约姆公路上。这三支队伍的先遣队恰好同时会合于市政厅广场;而从附近的各条大街小巷,德国军队还在源源到来,一支队伍接着一支队伍,沉重而整齐的步伐踏得路石笃笃作响。
用喉音很重的陌生语言喊出的号令声,在一排排看似无人居住的死气沉沉的房屋前回荡。在紧闭的百叶窗后面,无数只眼睛正窥视着这些战胜者。他们现在成了这座城市的主人,依据《战时法》,他们不仅有权支配他们的财产,而且有权主宰他们的生命。居民们躲在遮挡得漆黑的屋子里,惊惶万状,仿佛遇到了大洪水和毁灭性的大地震,纵然你有再大的智慧、再大的力气也无可奈何。每当事物的既定秩序被推翻,安全不复存在,受人类法则和自然法则保护的一切都任随凶残无情的暴力所左右的时候,人们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地震把一个民族全部砸死在倒塌的房屋下;江河泛滥卷走淹死的农民以及牛的尸体和脱落的房梁;或者获胜的军队屠杀自卫者,带走俘虏,以战刀的名义抢掠,用大炮的吼声感谢某个神祇,所有这一切都可谓令人恐怖的大灾大难。它们完全动摇了我们对永恒正义的信仰,也无法让我们如人们说教的那样去信赖上天的保佑和人类的理性。
三五成群的敌军敲开各家的门,然后进去住下。这就是入侵以后接踵而来的占领。战败者开始履行义务了;他们必须对战胜者百依百顺。
过了一段时间,最初的恐怖感消失了,新的平静气氛形成了。在许多家里,普鲁士军官和房东一家同桌吃饭。若碰上个有教养的军官,他还会出于礼貌为法国鸣冤叫屈,表白他对参加这场战争心里是如何反感。仅仅由于他怀有这种感情,就值得人们向他表示感激了,更何况有朝一日还可能需要他的保护。把他笼络好,也许就能少供养几个士兵呢。再说,既然自己完全捏在此人的手心里,跟他伤了和气又有什么好处?真要那么干的话,与其说是勇敢,倒不如说是鲁莽。而鲁莽这种毛病,鲁昂的有产者们再也不会有了,因为现在已经不是这座城市引为骄傲的英勇保卫战的时代了。最后他们还从法国人的礼俗中找出一条至高无上的理由,说什么对外国军人只要不在公共场合表示亲热,在家里尽可以以礼相待。于是,彼此在外面都装作互不相识,一到家里就兴高采烈地促膝而谈;那位客居的德国人呢,每晚和房东一家围坐在炉边烤火的时间也就越来越长了。
目 次
西蒙的爸爸
羊脂球
一家人
一个女佣工的故事
泰利埃公馆
菲菲小姐
瞎子
修软垫椅的女人
一百万
遗嘱
小步舞
骗局
骑马
两个朋友
在海上
米隆老爹
怪胎之母
花房
我的叔叔于勒
父亲
细绳
老人
伞
项链
索瓦热大妈
小酒桶
散步
归来
衣橱
图瓦
珍珠小姐
坑
爱情
流浪汉
奥托父子
港口
墓园野妓
莫泊桑的遒劲、简洁、自然的语言带着我们衷心喜爱的土地的香味。他拥有法兰西语言的三大优点,首先是明晰,其次是明晰,*后还是明晰。
——法郎士
请允许我以法兰西文学的名义讲话,作为战友、兄长、朋友,而不是作为同行向吉·德·莫泊桑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是在居斯塔夫·福楼拜家中认识莫泊桑的,他那时已在18岁到20岁之间。此刻他又重现在我的眼前,血气方刚,眼睛明亮而含笑,沉默不语,在老师面前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谦恭。他往往整整一个下午洗耳恭听我们的谈话,老半天才斗胆插上片言只语:但这个表情开朗、坦率的棒小伙子焕发出欢快的朝气,我们大家都喜欢他,因为他给我们带来健康的气息。他喜爱剧烈运动,那时流传着关于他如何强悍的种种佳话。我们却不曾想到他有朝一日会有才气。
《羊脂球》这杰作,这满含柔情、讥嘲和勇气的完美无缺的作品,爆响了。他下车伊始就拿出一部具有决定意义的作品,使自己跻身于大师的行列。我们为此感到莫大的愉快;因为他成了我们所有看着他长大而未料想到他的天才的人的兄弟。而从这一天起,他就不断地有作品问世,他高产,稳产,显示出炉火纯青的功力,令我惊叹,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源源而出,无限地丰富多彩,无不精湛绝妙,令人叹为观止;每一篇都是一出小小的喜剧,一出小小的完整的戏剧,打开一扇令人顿悟醒豁的生活的窗口。读他的作品的时候,可以是笑或是哭,但永远是发人深思的。
啊!明晰,多么清澈的美的源泉,我愿看到每一代人都在这清泉中开怀畅饮!我爱莫泊桑,因为他真正具有我们拉丁的血统,他属于正派的文学伟大的家族。诚然,决不应该限制艺术的天地:应该承认复杂派、玄妙派和晦涩派存在的权利;但在我看来,这一切不过是堕落,如果您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一时的离经叛道,总还是必须回到纯朴派和明晰中来的,正如人们终归还是吃那营养他而又永不会使他厌腻的日常必吃的面包。
莫泊桑在15年中发表了将近20卷作品,如果他活着,毫无疑问,他还可以把这个数字扩大三倍,他一个人的作品就可以摆满一个书架。可是让我说什么呢?面对我们时代卷帙浩繁的产品,我有时真有点忧虑不安。诚然,这些都是长期认真写作的成果。……不过,对于荣誉来说这也是十分沉重的包袱,人们的记忆是不喜欢承受这样的重荷的。那些规模庞大的系列作品,能够留传后世的从来都不过寥寥几页。谁敢说获得不朽的不更可能是一篇三百行的小说,是未来世纪的小学生们当做无懈可击的完美的典范口口相传的寓言或者故事呢?
先生们,这就是莫泊桑光荣之所在,而且是更牢靠、*坚实的光荣。那么,既然他以昂贵的代价换来了香甜的安息,就让他怀着对自己留下的作品永远富有征服人心的活力这一信念,香甜地安息吧。他的作品将永生,并将使他获得永生。
——左拉在莫泊桑葬礼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