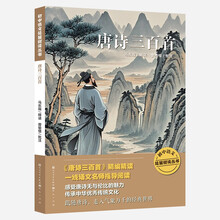还剩俩土豆。它们几乎都发白和发亮了,上面还有黑斑点,但我还是想吃一个,或者俩都要。我小心地伸出一只手。突然,感觉到小腿骨被踹了一下,禁不住眼前一阵发黑,不是因为疼,而是愤怒。但是我控制住了自己,很快地缩回手。“吃不到时,不要露牙”,我想起娄姨妈总是这样说。是杜罗从桌下踢了我一脚,她已经14岁了,比我高很多,和她打架占不到任何便宜,而且明年复活节她就要离开这里,回家去学做裁缝。她端起碗,让这两个土豆滑到她的盘子里,并把剩余的芥末酱全浇上。坐在桌子另一边的英格看到了这一切,她扬起眉毛,轻轻地耸耸肩。
这时,旁桌的乌尔班小姐站起来,开始摇铃。这是把暗黄色的铜铃,上面雕着花,镶着黑木柄,这铃总是放在她的盘子边。受到铃声的提醒,我们的桌子立即安静下来。之后一张桌子接一张桌子都安静了,最后食堂里鸦雀无声。
“大家注意听,”乌尔班小姐说,“五年级和六年级的姑娘两点半到手工大厅,全到!” 蕾娜特缩着身子坐在我旁边,她是唯一住在我们房间但上六年级的女孩。她看起来突然变小了,好像杜罗也踹了她一脚。但蕾娜特永远也不敢碰最后的土豆。
“你不用怕,”我悄悄地对她说,“手工大厅没什么了不起的,她只是在那儿和咱们所有的人说点儿事,也许是让咱们去美国远游,在密西西比河上划桴板。” 但蕾娜特并不觉得滑稽,也没笑。也许她从来没读过《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她的头埋得更深了。我生气和她说话,也为她本人生气。我根本就不想为她做什么,她应该一直闭嘴。我不强迫人,永远不!我的一个警句是:“不要笑还没有微笑过的人。” 今天既不该我擦桌子,也不该我洗碗,所以一点钟以前我就回到了寝室。坐在床上,用手指轻轻抚摩着小腿上的肿块,肯定一会儿就变青。这个胖妞!想脱鞋,却脱不下来。今天上午,讨厌的鞋带第三次断了,我在上面打了结,现在打结处穿不过鞋眼,只得又解开。我把鞋带的断头塞到鞋里,然后躺到床上。
我把脸埋在漂亮的红棕色的床罩里,开始想娄姨妈。我一直都只想娄姨妈。还有谁可想呢?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