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点到即止,用一种神秘而自得的眼神看了看鲍叔牙。这乍一听只是一句普通的戏谑之语,但鲍叔牙却深知内有缘由,只是碍于召忽在旁,管仲不得言明罢了。鲍叔牙转念一想:自己已决意荐管仲于公子纠,召忽便是同盟,对待同盟君子,若有所隐瞒,日后容易留下心隙,就不能产生百分百的互信。
于是,鲍叔牙极恳切地说:“我们这样说话,召贤弟恐怕听得云山雾罩了,我们的密筹,可以对召贤弟言明。他是位贤良方正的君子,现在已是公子纠的少傅,而你也是时候潜龙飞升了。”鲍叔牙喝一口蜜茶,接着说,“此次我特意让你们认识,是想我们能结成鼎足之盟,通过扶助公子纠而秉政,以兴盛我齐国。”
召忽素以万里之志自许,想不到一向谨厚的鲍叔牙和游溺于市井的管仲也是心怀天下之人,于是更加用心倾听。
“召兄的高就我也略有听闻,可喜可贺。”召忽忙谦逊地答礼。管仲接着说,“是这样的,令萱生于江汉巫筮之家,当然,家道在两三代前已破落,不再掌神祀之职。其家传一种鸟书文字,当今只有区区数人能读懂,这些可作通信之密码,即便信简被截获,外人也无从得知其义。”
召忽越听越糊涂,什么“巫筮之后”,什么“鸟书文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管仲看了看鲍叔牙,鲍叔牙再次深深颔首,示意他可以将计划和盘托出。
于是管仲继续说:“加上本次两个新设的联络点,在各国交通要隘之处所设的联络点总共有八个了。特别是郑国新郑和楚国郢都两处,更是重中之重,故近期有必要单独再设两个点,万一有个差池,我们还有另一处可用。”
“对,使他们互不相知,消息也可互相印证。”,鲍叔牙接着问,“以后关系重大的密信都用鸟书?”
“正是,平常仍用普通文字,只有重大之事方用鸟书。鸟书的对照翻本,各地都有了,我已交代好,紧急时要先毁翻本。”
管仲从袖中取出一卷帛书,想来就是翻本,将它轻轻交到鲍叔牙手中,鲍叔牙也不看,只谨慎地纳人袖囊里。
召忽听得出神,至此方才知道,原来管、鲍已在天下要隘之处密布眼线,而以经商作为掩护和经济来源,世人却从不得知,真是奇人奇事。他转而又想:以管仲的明智,用于经商可谓百战无不胜之理,而历来传闻他经商不善,并且常多占鲍叔牙的红利,看来也不过是障眼法罢了。此时,他更不敢小看管仲,也不轻易插话,只用心细听。
“此次我顺道去了宗周和新郑一带,可叹周室之没落已是大势所趋。”管仲缓缓说来。
“郑国呢?他可是一向自负为中国领袖。”鲍叔牙问。
“彼黍离离?”召忽想起刚才管仲吟唱之曲,他知道此曲之词出自《诗经》中的《王风》,讲的是一周大夫行役宗周,过故宗庙宫室,看到被犬戎入侵、大肆掠夺之后的残垣断壁,哀昨日之朝堂,今尽为禾黍,悯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而作此诗。虽然此地已赐秦伯,犬戎逐渐被驱除,但王畿萎缩,天子微弱,已形同虚设。各诸侯力政,皆叛而不朝,强者凌弱,战事不断,四夷崛起,交侵中原。召忽想到这些,不禁问道:“管兄,你看周室可中兴否?”
“唉,”管仲摇头叹了一声,“中兴是不可能了,苟延而已。”
“如果遇上明君良臣,加上贤德方伯之力,可再造大周否?”召忽有点不甘心地追问。
“此非人力之故,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夏传四百余年,殷传五百余年,大周亦有三百余年了,岂有长盛之姓?天道更迭,自是常识,天道则政道,故大周成也封建,败亦封建。”
“愿听高论。”召忽迫切地问。
“我太公辅文、武,伐无道之商纣,当时谁强谁弱?”
“当然是商强周弱,有道是‘大邑商,小邦周’嘛。”
“对,宗周兴于岐山,地狭人少,但负天命,得民心,众国来归,遂为西伯。灭商之后,关中、河洛几千里沃土尽为王室所有,可谓天下之至富之民、至强之兵俱集于此。但当时周人相对中国之大而言,还是极其稀少的,如要守土拓疆,唯有让亲属、功臣封土建国,以藩屏周室。”
“正是如此,这不是鼎定了大周繁盛之根本吗?”
“然则时过境迁,数百年后,原来的至亲已疏远为陌路,这是其一。其二,按‘亲亲’之原则,王室后裔不断繁衍,这后几代的王室子弟才是最亲的,但天子已无四边之地可封,如何为计?唯有将王畿的土地逐一分封给他们作采邑,采邑除了名称不同,一切与诸国无异。所以说一句僭越的话,采邑就像是周室身上的吸血水蛭,在不痛不痒之间,慢慢吸干周室的血髓。如今天下,枝强干弱,可见封建之法,决定大周必至衰亡,不可能再中兴,也决定大周不会像殷商一样,在尚强大时被革命,而是日渐衰竭,最后无声无息地灭亡。”
召忽从未听过如此之立论,断没有人能剖肤剥里地将玄之又玄的天道,从现实制度得失,简明扼要地理清因由。他不禁对管仲更加敬服,于是问道:“依管兄之见,此乱象还要延及数世,我齐国该如何自处?”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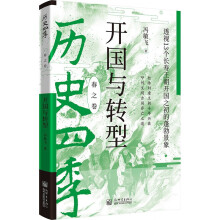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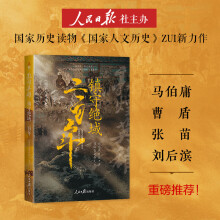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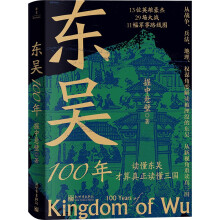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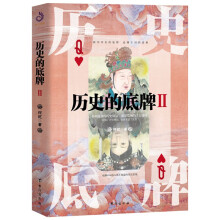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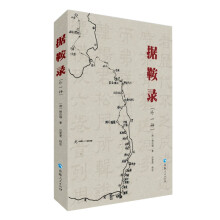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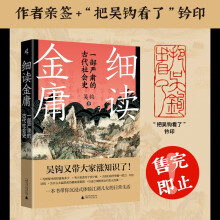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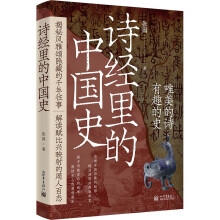
南夷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桓公攘夷狄而救中国。
——《春秋公羊传》
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一匡天下。
——孔子
(管仲)为政,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
——司马迁
无令管与鲍,千载独知名。
——李白
(管仲)中国较大之政治家,亦学术思想界一巨子也。
——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