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从豌豆尖开始的川菜
因为先生老家在成都,有些白目的朋友会问我“去他们家一定吃很多辣椒吧”,刚开始我还辩论几句,川菜的家常菜其实辣的也不是很多。后来我都懒得解释,在他们同情的眼光中不置可否地笑了。
川菜应是中国被复制得最广泛的菜系之一,但我在广州很少去川菜馆,个中原因,并非我恐麻惧辣或者畏油,相反我根本是个无辣不欢的狠角色。不去川菜馆,是不想让自己生气——广州几乎所有川菜馆的出品,而我又吃得起的,都是不合格的,它和我在家里吃到的成都妈妈的手艺未免差得太多。
街边低廉小馆味道或许略微接近,无奈食材质量实在太差,缺了蜀地“苍蝇馆子”出品的小聪明和大智慧,卫生情况更容易让人屙肚;高级川菜酒楼用料固然好,却又因无可避免地迎合广式饮食习惯而失了韵味和灵性;小吃总是错得离谱,担担面被彻底搞成宽汤面的行为令人发指;火锅连最基本的卤料底都熬不好,味道差了十万八千里……每次尝试都是失望而归,干脆断了念想。
更让人伤感的是,这些粗制滥造的东西竟然成了本地人对川菜的主体认知,觉得又油又咸又麻又辣就是川菜了,并且直接等于不健康。这种认知在广深一带你无法辩驳,但只要去巴山蜀地走上一圈,大抵就会自动放弃了。
用不着上到开水白菜的高度,仅仅是一盘鱼香茄子,就能让你感觉到川菜之美。在酸甜辣三味平衡的酱汁包裹之下,炸过的茄子紫黄相间,吃起来不仅口感丰富、香软甜滑,真味还一分不失,开胃下饭。鱼香茄子的重点是鱼香味酱汁的调制,需要用到泡红辣椒、郫县豆瓣、黄砂糖、陈醋、料酒以及姜、葱、蒜等多种配料,组合出异常丰腴的味觉体验。
鱼香味仅仅是川菜诸味中的一种,干烧、怪味、椒麻、红油、酸辣、陈皮、糖醋、荔枝、蒜泥等复合味型调味方式和佐料,给了川菜无穷的变化。当然,麻辣依旧是川菜的招牌,但做得好的川菜绝不会不讲道理地蛮干,你能明显感觉到麻和辣在互动,麻抑制辣,辣又能突出花椒特殊的香味,两者带有韵律感地在舌头上沉浮,却又能让食材的本味犹存,非常奇妙。想体验麻辣之韵,建议在成都试试麻婆豆腐,保证你吃得舒坦,全身每个毛孔还会打开来透气。
我所爱的川菜,是从头到脚都透着一股子精致的秀气。豌豆尖——豌豆发芽大约30天后摘下来的嫩苗——是个极妙的秀气代表。与粤菜常用的细幼豆苗相比,豌豆尖茎叶都粗大一些,但大约是水土不同的缘故,蜀地的豌豆尖生得极嫩,而且非常鲜美。豌豆尖可以清炒,也宜煮汤,但我最钟情的还是凉拌。豌豆尖稍稍过下滚水,捞起滤干放凉后,加蒜泥、麻油拌匀,滴两滴陈醋,再均匀地撒上盐就行了。这道川式沙拉有着强烈的春天情愫,入口即化,清甜无敌,非常雅致。
下次去吃川菜,不要急着点水煮牛肉、辣子鸡这些大盆大盆的大菜,多留心一下平时被忽略的小气菜,说不定会让你更加爱不释手。
没有灰色的大蒜
也不知道我这么洋气的人儿,怎么就这么喜欢吃大蒜。
曾在西安街头,穿得花枝招展地坐在一群本地大叔之间,面前一大碗水盆羊肉,一边用猩红的指甲剥蒜丢进嘴里,一边大块吃肉,爽快无比。吃潮州卤水鹅,绝对离不开蒜泥和白醋;若四川火锅没有蒜蓉麻油蘸碟,那离正宗还有十万八千里;蒜蓉炒各种青菜,各种百搭;无论是排骨、扇贝还是茄子,蒜蓉是与生俱来的好朋友;蒜蓉法包更是让这根硬棍子焕发了新的春天……我想象不出来如果没有大蒜,饭碗会变得多么乏味。
自从爱上韩国烤肉之后,又彻底地被大蒜征服了。尤其是牛舌,烤到刚刚变色卷起就夹起来,滴点柠檬汁,蘸上大酱,裹块蒜瓣送到嘴里,恰到好处的油脂香,微微的牛奶味,混着柠檬的清爽和大酱带来的厚重的黄豆气息,已经极端迷人。我更期待的是咬下去的那一瞬间,脆生生的大蒜立即给出反馈,生异香,鼻尖冒出一层亮晶晶的汗珠,浑身清爽,精神抖擞。
大蒜的原产地是地中海西岸,埃及、希腊和罗马人三千年前就爱上了这个玩意儿。中国人吃上大蒜,得感谢西汉汉武帝时期出使西域的张骞。估摸张先生也是我等烤肉帮同好,回国前觉得自己毫无舍弃西域美食的勇气,于是干脆把调料都配齐带了回来,不仅有大蒜,还把芝麻、蚕豆、黄瓜和胡萝卜一起打包了。有了好吃的张先生的探索,才有了丝绸之路,真的,吃的欲望是改变世界极重要的原动力。
蒜味很冲,冲到吸血鬼都怕这玩意儿。但就算把自己搞得满身味道,大蒜控们也浑然不知,还会有点恶作剧的沾沾自喜。哪知道身边的人早已忍了又忍,只敢屏住呼吸,大气不出地勉强保持笑颜。喜欢大蒜,自然也会钟情上它的三姑六婆:韭菜、洋葱、蒜苗、葱、藠头,如此种种。而且蒜是没有灰色地带的食材,爱的人甘之如饴,讨厌的人捂鼻鼠窜,并没法有“那今天我就勉强吃一吃好了”的心态,不暧昧,不苟且,普通的外表掩盖的是“如果爱,请深爱”的价值观。
若是你爱蒜又懒,更好的办法是把身边朋友都变成大蒜控:“吃大蒜好啊,降胆固醇,降血脂,杀菌清肠去毒素,还能除粉刺呢。”待周围都是臭人的时候,世界也就没有臭人了。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个小贴士:吃了蒜之后吃几颗花生米,可以迅速减少扰民的气味。
米的一百种形态
不得不承认,虽然无时无刻不在追求“洋气”二字,但能让我的味蕾彻底舒适放松的,还是某些土得掉渣儿的老祖宗的东西,比如老火煲汤,又比如米。
如果出国在外,长久吃不到米和米制品,我的精神会濒临崩溃。即使是一口也好,就是需要这一点点米的气息作为安全感的寄托。实在找不到中餐厅的时候,我会选择吃日餐厅,要一套鳗鱼饭定食,只求一碗热乎乎的白米饭,用碗装着,无害无辜的样子。曾在巴黎街头的寒风中看到别人吃越南河粉,看到坐在门口的人把一碟小辣椒倒进汤里,我的口水简直抑制不住一直涌出来,非常馋这口,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对食物穷凶极恶的渴望。
米这玩意儿的妙处不仅在救命安神,还能颇有趣味。潮汕人民把一切米制品都称为“粿”,可粿和粿之间又大有不同。最常见的形态是粿条,也就是宽条米粉,不仅能轻松完成饱肚的任务,在沙茶酱和花生酱的配合下,还可化身成熬夜加餐之绝世美味。把米浆摊平晾干,要吃时入锅煮开,再加一点点米浆或者生粉水,煮至半糊状起锅,此乃粿汁,米香扑鼻,甜滑舒畅,配上一盘传统潮州卤水拼盘,是我很推崇的下午茶替代品。
潮汕街头路边摊上蒸笼里的各种粿,更是妙不可言:小巧的凹字形如灯盏般的咸水粿,加上一点点熬得奇香的菜脯(萝卜干),风味相当清雅;混着桑叶汁的颇籽粿,一口咬下去,草本的天然之气迅速占领口腔,米香又提供了恰到好处的甜度和口感,实在妙极;包着绿豆或芋泥的鼠壳粿,用平底锅煎得略焦,又脆又糯,和伯爵红茶是绝配……即便被改变了形态,各种食材又把它装扮得千面不同,可米永远能保持着自己中立温和的特性,不添一分,不减一寸,让强烈的味道们尽情张扬,又有回身立命之地。
如果单要欣赏米之美,还是质朴的方法——半水半米的清粥为最佳。煮得半透明的米粒悬浮在同样是半透明的粥水里,或许点缀着些小气泡,热气从表面缓缓升腾,越是观察越会觉得面前的这碗粥有禅意。用木质筷子(勺子当然要方便很多,但出于尊崇禅意的一致性,我还是推荐用筷子)撩起一堆米粒,趁热迅速吮进嘴,先用舌尖感受粥的温度和稠度,随后放任它们在嘴里自由扩散,这时候最好把脑子放空,让温柔又清爽的米香从味蕾慢慢地向头顶涌去。
喝稀饭,嚼还是不嚼不应该成为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交给你的本能来处理就行。当温热的粥水顺着食道往胃里滑时,冥思暂时停止,是时候撩下一口了。和品酒一样,试试不同品种的米,用不同火候和不同水量,或者用不同炊具和不同烹饪时间做出来的粥,你会发现完全不同的结构和香味,而且颇有怀古之风。
即便是最简单的食材,只要用心品鉴体会,也能成为一门艺术。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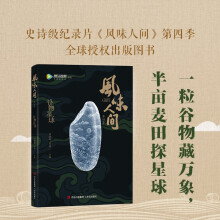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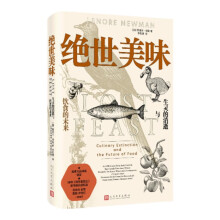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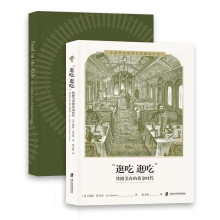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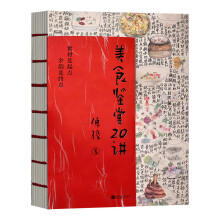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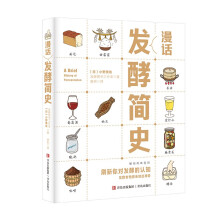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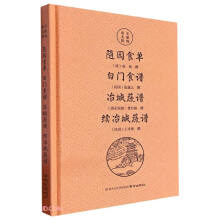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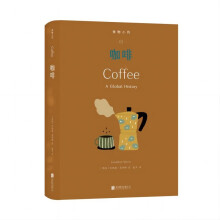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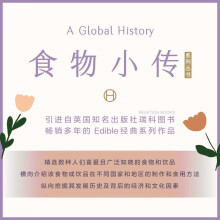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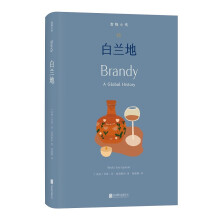
——网友 曾玩玩
“看她的文字仿佛可以闻到一股香气,有感官效应。”
——网友 Shank不是我的英文名
“她很有魅力,表面上好笑,看似刻薄,但骨子里很善良正直,聪明能干也勤奋,我喜欢这样的人。”
——网友 Summer
“大咖的娓娓道来,深深地说出了天蝎座的内心戏。坚定、执着,无论这个世道怎么讨厌,它都是个冒傻气却难能可贵的品质。”
——网友 老河水妖
“生出各种回应。这种自在,好生羡慕,娇俏如你。”
——网友 伟文大义
“吼!最喜欢掏心掏肺美艳洋气说话准狠快的美少女嘞!”
——网友 杨小鲸
“一向都觉得,陈大咖把我们很难抓到的感情给描写出来的功力太强了。总会有‘就是这样’的感叹。”
——网友 用鸡眼看天下
“洋气又心软,这个泪点超低的家伙,爱从她的角度听故事。”
——网友 咸蛋菜心粥
“大咖是珍珠一般的存在,温润可爱,灵气闪闪,以不灭的光芒指引着一众岭南吃货。”
——网友 Hel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