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以为博物学自19世纪之后便已销声匿迹,而博物学家只是业已灭绝的化石级生物,戴维·乔治·哈斯凯尔会告诉他:事实绝非如此。恰恰相反,博物学家不但接受了自然选择和演化论,而且在现代文明的空气和土壤中茁壮成长,悠游自在。
博物学家是一个个体特征各异的类群,正如博物学是一门相当广泛的学问。普林尼时代,博物学家以“虫鱼草木之名”为宫廷里的小王子启蒙;斯多亚学派的博物学者假借自然事物以讽喻世人,中世纪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近代以降,波澜壮阔的地理大发现,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让博物学家在远征的舰船上赢得一席之地:整个17、18世纪,博物学家一面为新兴的帝国经济寻找新的契机,一面忙着搜罗材料为古老的自然神学大厦添砖加瓦;19世纪中后期,当工业革命的推进促使人类文明的触须急速伸向自然界中各个角落时,博物学家开始将目光转向荒野,从中寻找救治“现代文明病”的良方妙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博物学家占据着不同的“生态栖位”。万变不离其宗的是:这是一群以观察、记录和描述自然事物为己任,并且乐在其中的人。
然而,当对外扩张已经到达世界的尽头、发现新物种的可能性日渐减少,博物学家的使命是否已经终结?发现的乐趣该从何处去寻觅?而当现代生物学要求以冷静客观的科学态度看待研究对象时,新生代的博物学家又该如何处理那些让他们显得“多愁善感”的情感共鸣?作为新生代博物学家的作品,《看不见的森林》对此做出了回答。
《看不见的森林》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呢?从内容上来说,它是一位美国生物学教授开授的生态学课程,也是一部翔实的物候观测笔记;从形式上来说,它更像一部科教纪录片,由一帧帧流动的、色彩鲜艳的画面构成;而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它是丛林版的《所罗门王的指环》,也是写给成年人看的《少年哥伦布》。尽管哈斯凯尔像以往的博物学家一样,选择了-一个相对“远离人类文明”的场所,即美国田纳西州一片老龄林中的方寸之地,但是他也告诉我们,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能找到这么一块安详宁静的“圣地”固然是幸事,如若不然,也不妨碍博物学观察。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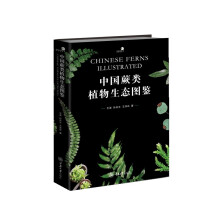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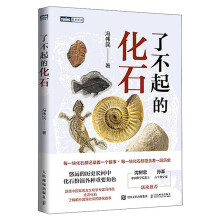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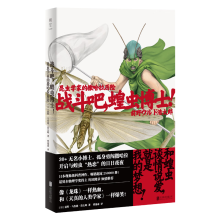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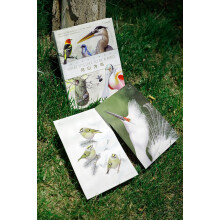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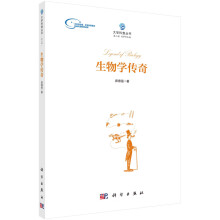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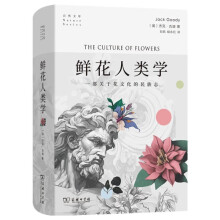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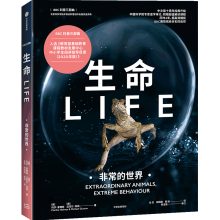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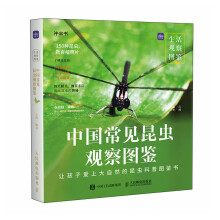
——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Wilson),哈佛大学名誉教授
★戴维·哈斯凯尔在坎伯兰高原上一米见方的小天地中锻炼自己的观察能力,在此过程中,他如同以往任何作家一样,清晰地看到了整个富有生机的地球。义中的每个章节,都会教给你新的东西!
——比尔-麦吉本(Bill McKibben),著有《即将到来的地球末日》
★在这些篇章中,戴维·哈斯凯尔以利奥波德、约翰·缪尔和梭罗的笔法,刻画出演化过程中的美与复杂。对那些希望多到野外去找灵感的人来说,这本书是非常理想的随身读物。哈斯凯尔非常了解森林以及林中的生灵。他渊博的知识给野外探险者提供了指南。散文的写作风格,与自然研究中所觅得的诗意宁静相得益彰。这部著作堪称一部真正的博物学家宣言。
——格雷格·格拉芬(Greg Graffin),著有《无政府状态的演变:无神世界中的信仰、科学和坏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