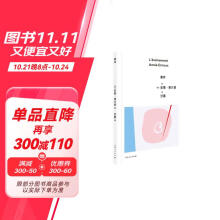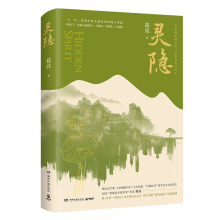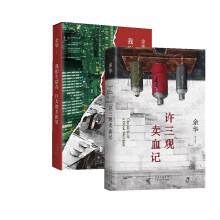《煤河情仇》:
光绪七年的夏天,天格外热,整个冀东大地,仿佛被一个巨大的蒸笼笼罩着让人们难以喘息。在冀东东部有个叫婿嫁庄的小村,村子虽然小,却有些来历。相传,明朝永乐年间,赵氏祖先由玉田彩亭桥迁至王禾庄,因为兄弟分家另过,弟弟被王禾庄南边一个无名小村的独女户招赘为婿,打那以后,这个村便取名婿嫁庄。
进入“二伏”的时候,天更热了。婿嫁庄村东头“陈记烧卖铺”笼屉中的那些烧卖像患了哮喘的病人一样,费力地喘息着,不停地从褶皱的缝隙里冒出白腾腾的热气。那些平时在集市的肉案子下钻来蹿去、捡拾骨头和碎肉的流浪狗们,也都懒懒的趴在墙根或树阴底下,伸出长长的舌头,贪婪地呼吸着燥热的空气。地里的庄稼,同样忍受不了这样的天气,已经从土里钻出一大截的青苗像要着火似的,它们试探着刚露出地面,就被炽热的太阳晒枯萎了。所有的坑塘河沟里没有一滴水,往年一到夏季就开满荷花的莲子坑,也露出了多年不见的河床。河床上满是龟裂的干泥块,泥块之间的缝隙,几乎能伸进大人的拳头,远远看去,就像挤满了许多乌龟一样。房前屋后的柳树和槐树的叶子,开始变得枯黄,用脚一踹树干,叶子便沙沙地掉落到地面那些干枯的小草上。在这十年九涝的地方,人们常说连蛤蟆撒泡尿都会把庄稼泡在水里,可是这一年的旱灾却是让这些庄稼人百年不遇的灭顶之灾。人们企盼的丰年已经没指望了,等待他们的将又是一个拉队逃荒的年头。田地里,那些和地主签了“死租”契约的佃农们,来到田地里看着快要着火的青苗,立刻放下手里的锄头绝望地看着快要死亡的庄稼。人们的脸上都现出一样的沮丧,人们心情都是一样的复杂,当然,人们的结局也都将是一样的悲惨。人们相互打着招呼的时候,都说着同一句话:“完啦,又是一个搭帮要饭的年头!”百年不遇的干旱,让整个冀东大地变得死气沉沉,腥臊闷热的空气中,蝉鸣像是在演奏悲凉和死亡的乐章,只有那些还不懂生活艰辛的孩童,仍在无忧无虑地玩耍着,他们有的把蜘蛛网绕在用高粱秸秆做成的粘网上,然后悄悄地把长长的秸秆举过头顶,对准树上一只正在颤动着翅膀鸣叫的知了猛地拍下去,随着知了被黏黏的蜘蛛网黏住后在网上不断挣扎,干枯的树叶也哗啦啦地散落到地面。还有的孩子,或坐或站在往年清澈见底的河床上,时而嬉戏打闹,时而背诵着那首流传已久的冀东童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门口唱大戏,接闺女、叫女婿,外甥外甥女也要去。没啥好吃的,高粱饼子炖鲤鱼!”这些天真的孩子们还都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和大人们手拿讨饭的棍子,走上背井离乡的逃荒之路……
第二天早晨,滚烫的土地还没有退热,太阳却又早早出来为大地加温了。似乎一切生物都难以承受这干旱与闷热,天上悬着的太阳就像一个硕大的火球,炙烤着世间万物。但是,就在这百年不遇的干旱年景里,婿嫁庄通往西部挡水围子的土路两旁,仍然存活着一排排柳树。由于这里的地势东高西低,导致东部旱情严重,而西部则要稍好一些。即使这样,道路两旁那些仍然活着的柳树也像刚刚交完租子的佃农一样,蔫蔫地打不起精神。柳树细细的枝条垂落到地面,随着带有腥臊味道的热风来回摆动,躲闪着落在它们身上的各类昆虫。寻着远处吹来的一阵热风向远处望去,寂静的土路上只有一辆花轱辘大眼车,正沿着垂柳覆盖的土道上缓慢前行。到近前一看,只见车上坐着一男一女,赶车的男人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壮汉,黑脸、厚唇,浓眉下长着一双黑亮的大眼睛,脑后粗黑的辫子,甩在胸前。他上身穿一件粗白布短袖袄,随着他的不断喘息,穿在身上的衣服被壮汉隆起的肌肉撑得满满的,当他举鞭驱赶牲口的时候,那紧包在身上的衣服像是要被撕裂一样,紧紧绷在他那壮硕的身体上;年轻壮汉的下身穿一件毛蓝裤子,千层底的套伐鞋上的布靴套,紧紧地包裹着两只粗壮、结实的小腿。总之,这个年轻车把式的整个身体,无不显示出硬朗和壮实。与车把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端坐在车厢里的漂亮少妇,在这个壮实的男人的衬托下,年轻女人显得格外清秀。只见她盘腿坐在车厢中间,如墨的发问梳着一个小篹,篹上别着一枚精致的银簪,这是她由姑娘变成少妇的标志性变化。少妇面庞清秀白皙,细眉下长着一双会说话的眸子,她上身穿一件浅色缎面偏襟小袄,下身穿一条深色长裙,总之,少妇就像冀东平戏里表现的传统美人一样,看着就招人喜欢。车的颠簸,让少妇不断地在车上调整坐姿,一双丰满的乳房随着大车的颠簸在胸前不停地颤动,长裙下的三寸金莲小脚也时而露出裙外,虽然车上只有两个人,但是少妇还是不时地用裙子遮盖,少妇的漂亮迷人引得车把式不住地回头张望,然后又转回身赶着牲口继续前行。走了一段路,大车开始有些颠簸,这时,车把式一边轻声召唤了一下拉车的牲口,一边关切地回头看看正在闭目沉思的少妇,当他看见少妇的深色套裙下露出一双娇小的绣花鞋时,车把式忍不住伸出手轻轻捏了一把。顿时,少妇从沉思中蓦然惊醒,她羞涩地推开那双粗糙的大手,嘴里发出细细的声音嗔怪道:“看你,真没羞!”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