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救距离》:
烟灰缸放在小桌板下面。我拉出抽屉,把烟灰缸递给她。
“大卫在大约六年前生了一场大病。当时正是棘手的时候。我开始在索托马约尔家的农场工作,那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我在那里当会计,尽管说实在话我其实对会计一窍不通。这么说吧,我其实是在那里做些案头工作,整理文件,帮忙加加减减算数什么的,但我很喜欢那份工作。我每天穿得整整齐齐的,走去那边处理各种文件。你们这些首都人可能不理解,在我们这里,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需要找一些理由,‘为了工作’这个理由对我来说最理想了。”
“你丈夫呢?”
“奥马尔养马,你应该听别人说过。奥马尔是另一种风格的。”
“我昨天带妮娜出门散步时好像看见了你丈夫。他开着一辆小卡车,我们跟他打招呼,他没有回应。”
“是的,奥马尔现在是这样的。”卡拉说着摇摇头,“当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还会笑笑。他的工作是养赛马,养在镇子的另一头,湖的后面。但当我怀孕后他就彻底搬过来了。这里是我父母的房子。当奥马尔决定搬过来后,我们拿出所有的钱,把房子整个装修了一番。我想在地板上铺上地毯。没错,就我们的情况而言,这种想法非常荒唐,但这是我的梦想。奥马尔养了两匹名贵的母马,它们生了两匹小马,叫‘悲伤猫’和‘细;羚羊皮’,这两匹马已经卖掉了,至今还在服役,在帕勒莫和圣伊希德罗参加比赛。之后它们又产下另外两匹赛马,还有一匹小马驹,但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要做好这门生意,你得有一匹好的种马,奥马尔借来了一匹最好的。他在母马的地盘后面给小马驹单独造了一个围栏,种上苜蓿,一切准备妥当后,他才开始安安静静地装修马厩。他签了一个协议,把种马租来两三天,等小马驹出生后,卖掉的钱有四分之一归种马的主人所有。这可是很大的一笔钱,如果种马足够优秀,小马驹又养得好,每只小马驹可以卖出二十万到二十五万比索。因此我们带来了这匹种马,奥马尔成天看着它,像僵尸一样跟在它背后,数着它上了每只母马多少次。等我从索托马约尔回来他才能离开,然后轮到我来当班,我在厨房里,不停地从窗户后面往外看,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问题是,有一天下午,我正在洗碗,忽然意识到我有一阵子没看见那匹种马了。我跑向另一扇窗户,然后又看了另一扇,从我最后一次看见它的地方开始往后找,但一无所获:那些母马还在,但哪里都没有种马的影子。当时大卫刚开始学走路,我走到哪儿他都要跟着我;于是我一把抱起他,冲出门去。我们这里地方不大,一匹种马应该是很显眼的,找不到就是找不到。很明显,那匹种马不知怎么地跳出围栏去了。这很少见,但这种情况也确实会发生。我跑到马厩,向上帝祈祷马还在,但那里也没有种马的身影。我想起了镇上的小溪,它很小,但是位于山下,如果一匹马跑去那边喝水,从家里是看不见的。我还记得大卫在问我怎么了,于是我出门前一把抱起他,他环抱着我的脖子,在我大步往外冲的时候,他的声音在我的耳侧两边回想。‘在那边,妈妈。’大卫说。于是我看见了那匹种马,正在小溪旁喝水。我向下跑去,大卫想下来自己走,于是我把他放到地上,叫他不要靠近那匹马。然后,我蹑手蹑脚地走近那匹种马。有几次它躲开了,但我保持耐心,继续靠近,终于,它对我放下了戒心。我一把抓住了它的缰绳。我至今还记得,当时自己是多么地如释重负。我长吁一口气,大声对它喊‘如果你丢了,我们会倾家荡产的,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你看,阿曼达,这就像我当时觉得大卫少一根手指的事情一样。你会觉得‘破产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然后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届时你宁愿用家产、用生命来挽回这一刻。如果时光倒流,我一定会放开那该死的畜生的缰绳!”
这时我听到客厅的沙门被拉开的声音;我俩一齐望向房子的方向。妮娜出现在门口,抱着她的鼹鼠玩偶。她还有点儿没睡醒,意识蒙胧,所以虽然她到处都没看见我俩,却也并没慌张。她一手抱着玩偶,一手抓着扶手,小心翼翼地走下门廊前的台阶,踩到草坪上。卡拉重新靠回座位上,默不作声地从后视镜看着她。妮娜看着自己的双脚。从我们到这儿以来,她一直喜欢玩这个游戏:在草地中伸展和蜷曲自己的脚趾头,牢牢地抓住地面。
“在那时,大卫在小溪里蹲下了。,他的鞋子全部被溪水浸透,双手浸在水中。然后他开始吮吸自己的手指头。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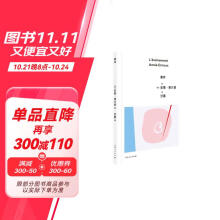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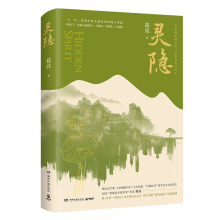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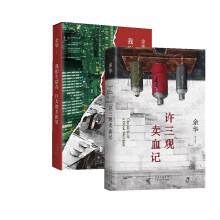







——《纽约时报书评》
★萨曼塔·施维伯林的声音在当代西班牙语文学里独树一帜,我期待听到更多她的讲述。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2017年度布克国际文学奖入围作品《吃鸟的女孩》作者新力作
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的豆田,看似宁静却埋伏危机。阿曼达经历的是梦魇,还是真实?
我记得五岁时我就给我妈妈讲“睡前故事”,我还不会写字,就让妈妈记下关键情节,留出空白,到了白天我会把插图补上。
——萨曼塔·施维伯林
★我记得五岁时我就给我妈妈讲“睡前故事”,我还不会写字,就让妈妈记下关键情节,留出空白,到了白天我会把插图补上。
——萨曼塔·施维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