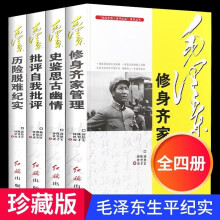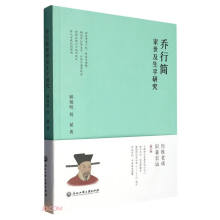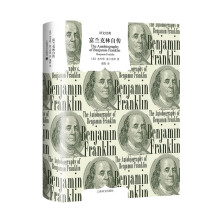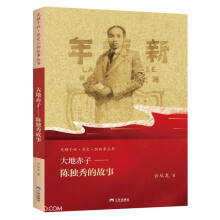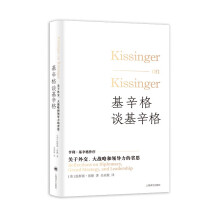《吴为山/政协委员履职风采》:
一、寻梦:为理想求索
我出生于苏北里下河地区时堰镇的一个书香世家。这个文化古镇,历史上出过一些名人,如清代水利学家冯道立,第一个提出教师节的教育博士邰爽秋等。从刚记事时起,我就在街上看到那些算命打卦的先生、为人治病整牙的郎中和专画遗像的画师……小镇青砖黑瓦,商铺一家挨一家,药房、笔庄、钟表行、布行、米行……一条石板街,热热闹闹。悠长绵延的串场河,流经古镇,将黄海之滨的盐运向扬州,估计当年“扬州八怪”活跃时的盐商便是从这条河源源不断获得生财之道。河上波光粼粼、白帆点点,捕鱼的,烧藕的、捉螃蟹的……
多年来,家乡的淡淡的、悠悠的印记常常在我的梦里。父亲1929年生于溱潼镇望族高家,小时候常听他说,我的曾祖父高也东为清末秀才,伯祖父是当代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高二适先生,父亲因出生后便过继给其姨母家,故姓吴。养父吴敬梓知书达理,善良诚恳,满腹经纶,我童年时也常听他讲故事。
父亲吴耀先自省立如皋师范毕业后即参加革命,任解放区高小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入大学深造,数十年来,坚守讲台,教书育人,并酷爱书画,擅诗词笛箫。外祖父乃开明绅士,我记得家中所用瓷器皆有当年景德镇工匠为外祖父制作的字样。我们弟兄姐妹七人,二姐在上世纪80年代病逝,我排行老五。大约在五六岁时,我开始喜欢家中藏的古书中的插图和陶、瓷器皿上的画作,那些清雅的山水和古香古色的仕女图刻在我深深的记忆里。1969年随父母下放农村,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在广阔天地间,受父亲的熏陶,11岁的我就摸索着写生,画小镇上熟识的老人。那时,知识界受到巨大冲击,传统文化更是不受重视。在那样的社会氛围下,我的父亲依然要求我每天早上先背诵一首古诗才可以去上学。1977年,随着招生制度的恢复,予“下乡知青”“回乡知青”和正在读书的中学生以无限的希望。“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大多数插队农村知青夜以继日补习功课,加入了高考的行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成了时代的普遍追求。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号召所有年轻人都向科学进军,我也响应号召,放弃了一直喜欢的绘画,而选择学习理科,并立志学医。我参加了1978年、1979年的高考,都以一分之差落榜,大学梦成了泡影,我彷徨、消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意识到艺术道路也许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选择。因为招生志愿表有“美术”特长的记录,我被录入无锡工艺美校学泥塑,在那里接受艺术教育,使我在人生起跑时,明确了生命的航向,从而走上了艺术的道路。
为此父亲作诗,以击鼓催发,亲自送我过长江到了惠山脚下求学,从此我攀登艺术之峰有了始点:
求医失路笑难关,
从艺有期莫等闲。
坐井观天终是小,
大江放眼快扬帆。
无锡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顾恺之、倪云林、王绂……太湖、惠山、江南民居……自然与人文的重奏使我对未来前景寄予希望。近代工商业的发达,让这座城市富庶而美丽,闻名海内外的无锡惠山泥人也给我的专业学习带来信心。
学校在惠山脚下,说是一所学校,其实原是一个祠堂,后由于修建,成为惠山泥人厂的仓库,经改造后作为校舍,一间大教室隔成两个空间,50个学生分成两个班。教室专业课与文化课同在一起。画室陈列了许多石膏像和石膏几何体教具。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塑像:维纳斯、米开朗基罗胸像、伏尔泰、亚历山大块面像……画室外的小庭院堆了些惠山土,是制作泥人的原材料,那油性的泥土润泽而富有柔性。西洋石膏像的洁白和惠山本地泥土的乌黑形成强烈反差,它注定了我的命运与之紧密关联。从参加理科高考转向学习艺术,从大学梦到进入民间泥人学校,这对我而言需要在心理和学习方法、生活习惯诸方面调整。好的是,第一节课由吴开诚老师讲素描,其精炼、扼要的讲授与娴熟的绘画演示令我一下子感受到艺术世界的灿灿阳光,感受着那些塑像在人类文明的造化,我逐步在这小小的“祠堂”中安心下来。学校几位专业老师和行政领导对我们关怀有加:素描与图案、彩绘、工艺美术史、语文、文艺理论、国画、书法和水粉画等课程均有敬业的老师教授,学校学习氛围很浓。吴开诚老师经常于星期天来学校画素描和色彩写生,多以班上同学为模特儿。他善于用铅笔勾线辅以明暗,线画过后,稍用手擦,对象神形便出来了。他的舅父是中国早期留法画家蒋仁,吴老师受其影响,素描有法国味道。这味道大致来自古典的严谨、单纯,颇有安格尔的遗韵。这种方式和画法在当时并不多见,因“苏派”明暗、块面的“科学方法”占据各院校素描教学。吴老师强调表现对象要有真实感受,不要有“习气”,要训练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和培养艺术的感情。我们不少同学学习吴老师“擦”的方法,但他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擦不是目的,不要简单学习表面上的手法,擦要擦出结构和形体。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