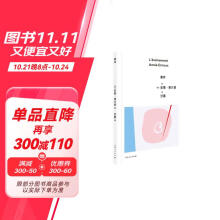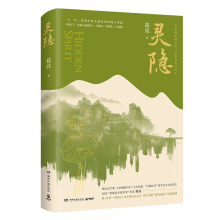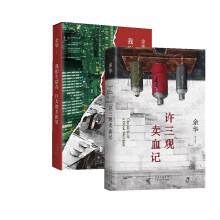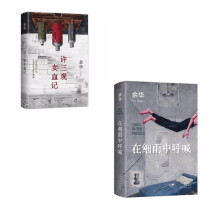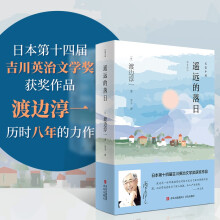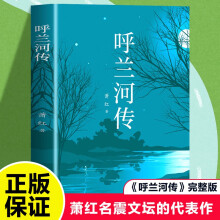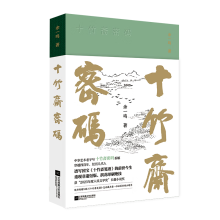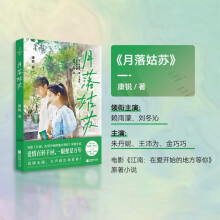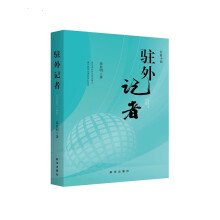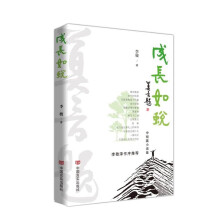《大商道》:
一年一年,一月一月,一个一个,一茬一茬,不几年,半大小伙子已能撑破平丘坳的大小房屋了。若或居宅小没地方住的小孩,也就只好打小就找几个脾味相投的合挤在某一家的大炕上,你挨着我,我挤着你。你听惯我的呼吸,他闻惯你的响屁。你捶我掐他呼噜,不知不觉,就是一个天亮。不知不觉,这群平凡的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不平凡的火红年代的孩子也就在懵懵懂懂的革命洗礼中长大了。
除了清楚明白地缺衣少穿外,没人说清他们是怎么长大的。
人口增多,给本来不靠河远离海,可耕土地也就那么一小片的平丘坳,压上了沉重负担。
本来嘛,一个几百年都未见富裕过的小村庄,突然增多这么些毛头小伙子,这衣食住行之事又是计将安出?实在窘迫得无计可施时,有些人家也或偷偷摸摸窜到村西头与原来西丘坳交界处那座早已破败不堪、墙倒屋圮仅仅依稀可见“彻底扫除封资修”字样的半座不知哪一位神灵泥胎雕像跟前毕恭毕敬烧一炷香,磕几个响头,作几个揖,口里默叨几句似或神灵保佑诸如此类的祷词希求神灵保佑渡过难关的唯心事来。当然,这是极危险的举动,一不小心,就要论以迷信落后思想而与那几个不识好歹居然未经允许而私下将自家猪仔或果蔬卖与邻家的投机倒把分子一道去坐班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严重的或有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
好在平丘坳极难划分出地富反坏右的清晰界限,运动归运动,斗争并不那么激烈,数百年一成不变的亲谊关系并没遭受历史性的破坏。而这里的人们传统上习惯的也沿袭着“儿多不怕粮,山大好聚狼”的口歌儿。尽管从人口论的关系分析,这里人口突然增多,肯定的一点是天下太平。天下太平,繁衍生息,人们才有那个消闲劲儿。问题是当人口过剩,而且人们在哭饥喊饿时,眉宇间那道刀刻斧凿般深陷的皱纹,也就锁得更紧。
这里也有一所学校。由于平丘坳一直就那么几十户人家,只能办一所民办小学,这还得益于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国家普及义务教育政策。这里的孩子读得好的,顶多也就五年级或小学毕业。
其实,跳出平丘坳往大里一看,嗬!你还真傻眼:一望无际的大平原。
不知这里的先民是怎么想的。他们的列祖列宗却怎么就不能走出平丘坳几步,向外望上那么一望呢?难道这里真是有块吸人石,吸住了他们祖祖辈辈不敢越雷池一步的脚腿,硬生生杂姓群居相安无事就是这么几百年?尽管外界传说,这里有一处至今无法确定究竟能够在哪个方位或在哪个山丘下面找到的无穷的宝藏,这里的人们代代相传扎根这里实则是为了保护抑或是找到这座丰富宝藏。传说归传说,即便直至现在也并不见落实。
那么,历代传承不辍的个中缘由,无人说得清。
说起学校,离平丘坳不远的地方,也就十里八里顶多二十里的样子。周围初中竞有好几所。然平丘坳的人们似乎从血管里就习惯了那种自耕自作,自饮自食的生活习性。就是认定一个死理儿:咱们的娃没那个福气,念再多的书也还是农民一个。其实,这话就有些牵强。你不供孩子上学,无知的孩子又哪里懂得念再多书是农民还是干部的命的道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