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立生活》:
真的忘记了,从哪儿得到了这样的启示,这个启示像一颗青稞的种子,在我脑海里顽强地生长起来,我被它诱惑着,变得惶惶不可终日。我压抑着这个启示带来的热情,就像情人压抑着夜夜难眠的兴奋。然而,就在我遇见神女的那个晚上,那种热情像是压力超标的锅炉蒸汽,终于不可遏制地冒了出来,我想,我看起来应该像是一辆老式的蒸汽机车,笨拙和不耐烦地行进在被划定的轨道上,周身笼罩在一片白茫茫的雾气与嘈杂刺耳的汽笛声中。
神女的大名我早就听说过,一般来说,她是一个诗人,虽然她的诗我从没看过,但这并不妨碍她在我心目中的诗人形象,也许女诗人这个形象本身就索取着大量的想象力。不过,意想不到的是,那个晚上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却告诉我,她是个画家,喜欢画油画,她家已经差不多是个专业的画室了。这让我很迷惑,我想追问一下,却及时刹车了,因为我们并不熟悉,轮不着我多嘴多舌。一个陌生人咄咄逼人地要她承认她不是个画家而是个诗人是个傻到极点的事情。我沉默了,保持着礼节性的微笑。
沉默令人痛苦。神女大名鼎鼎,自然身边不乏谄媚者,其实我也渴望成为那样的谄媚者,但遗憾的是,自己的能力不够,在关键时刻我怕自己会变得张口结舌、毫无乐趣,因此,我有绝对的自知之明,我蛰伏在人群的一角,暗暗关注着神女,等待着突如其来的机会。是的,我像条阴险的蝮蛇。
机会总会赐予有准备的人,深夜的时候,机会出现了。那天吃完晚饭已经很晚了,但大家热情不减,面对着残羹冷炙还喝了许多酒下肚,直到饭店打烊,我们才被迫离开了“战场”,八九个人在大街上像酒鬼一样晃荡了很久,然后有人提议去唱卡拉OK,大家纷纷叫好,好像第一次知道有此等好事,实际上,昨晚很多人就是在KTV度过的,但他们太清楚灯红酒绿的城市实际上是非常贫瘠的,他们必须对有限的娱乐寄予深切的厚望。
大家保持着伪装出来的热情向KTV走去,但是在半路上,出现了状况。神女站住了,她转头对大家说:
“我就想在这里唱歌,这里多畅快啊!”
说着,她便坐下来了,她的身后便是经过园丁定期打理过的城市绿化带,一些整齐却低矮的灌木丛里黑黝黝的,特别适合野猫野狗寄宿。这一刻,我的心情是兴奋和复杂的,因为这落实了我对她的判断:她是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画家,画家中自然也不乏自由率性之人,但这种情怀是诗人的专利,“诗人情怀”是一个组合起来的形容词。……至于说复杂,是因为我隐隐预感到有机会了,却还不知道这种机会的踪迹在哪里,又如何去把握。
“好啊,”我当机立断,也站住了,看着神女大声说,“这个提议太棒了,我非常赞同,太有创意了!”
她看了我一眼,很高兴有人响应她,让她对自己的影响力有了一个确证。我为自己第一个充当了这个确证而感到幸运。这时候人群开始骚动,看来并非所有人都喜欢这样率性而为,因为他们都不是神女这样的诗人。挣扎、辩论与协商的结果是,队伍分裂了,一部分人继续向KTV进发,他们执着地要在现代化设备下一展歌喉;另一部分人和我一样,选择了和神女待在一起,留在街边当流浪的吉卜赛人,为这个城市守夜。尽管,留下来的人还不少,但毕竟比刚才少多了,我数了一下,正好有五个人,这个数字很好,有人群的热闹,也有每个人都接触的机会,进可攻,退可守。甚好。
我紧挨着神女坐下来了,神女望着我露出调皮的笑意,她小但美丽还有种激情,像略微激动的春风。我知道她这是在鼓励我,我的胆子略略放大了些。说实话,直接坐在地面上的感觉并不好,但她的笑声比椅子还令人舒服。我坐在她的笑声上,对她笑着说:“你再怎么伪装,诗人的本质还是露出来了。”她捋捋头发,笑着,不置可否,突然对我说:“可惜这里没有洒,有酒的话就完美了,比KTV完美多了。”这话对我宛如懿旨,我马上又无反顾地说:“这有什么,我马上就去买。”她撩了撩头发说:“你一个人行不行?”我壮着胆子说:“也许需要你的帮忙,要不我们一起去吧,主要的重活交给我就好了。”她吐了吐舌头,马上就站起来了,说:“走!”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有些张皇失措。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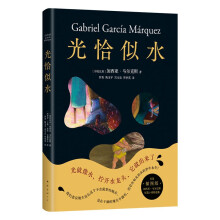







王威廉的小说,令人瞩目的,是他试图将抒情与哲学进行无缝的焊接,对虚无与绝望做出惊心动魄的反抗。这便形成了他的开阔气象。
——作家 毕飞宇
王威廉总是对生活保持警觉,寻找剖示人性的独特角度与切面,挖掘故事套路和流行话语所深埋的陌生感,形成一种哲学逼问。这种大志向和大眼界,在文学成功人士们拥挤的潮流中非同寻常,再次确证了写作的尊严。
—— 作家 韩少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