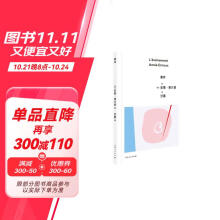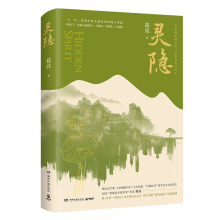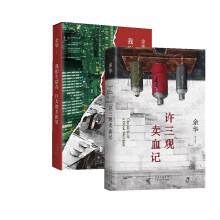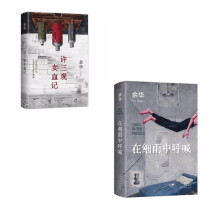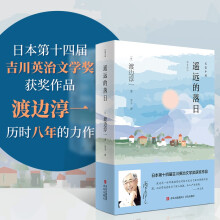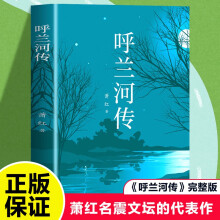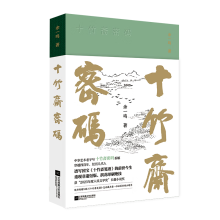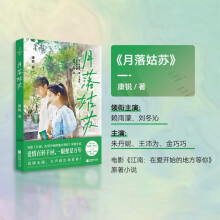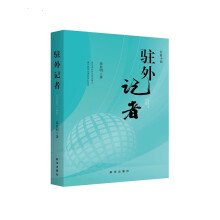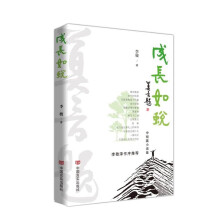波伏娃:一个成为标本的女人
从1999年在青岛第一次读到波伏娃的《越洋情书》至今,十几年的岁月过去,其间我陆续读了她的《第二性》《女宾》等作品,直到最近读了《美丽与叛逆:波伏娃画传》《波伏娃:激荡的一生》这两本传记,波伏娃的形象才在我心目中渐渐变得完整了起来。《美丽与叛逆:波伏娃画传》的作者是钱秀中,这本书2005年出版,主要的参考书目是波伏娃的作品,特别是她足足有四大卷的回忆录。而《波伏娃:激荡的一生》的中译本于2009年出版,原著作者是法国人克洛德·弗朗西斯和弗朗德·贡地埃,“这部作品也是波伏娃生前唯一认可的传记,资料分别来自传主的作品、与传主的访谈对话录,尤其是晚近发现的多达一千六百多页的与美国情人艾格林的通信”。
我最早读的《越洋情书》就是波伏娃写给美国情人的书信集。不管是直接翻译外国人写的波伏娃传记,还是中国人根据波伏娃的翻译作品给她写传记,因为经过了一道翻译,人名的翻译就很难统一,除了波伏娃和萨特在世界哲学史、文学史上早已赫赫有名,连波伏娃的这位著名的美国情人在中国的译名都不一致,一本书叫奥尔格伦,另外一本叫艾格林。
“西蒙娜·德·波伏娃于1986年4月14日逝世。围绕着她的作品和生活,激情从来没有消退,聒噪之声从未停止”,《波伏娃:激荡的一生》一书以此句收尾。三十年过去,在我这个理科生看来,波伏娃已经成为女性世界的一个标本,浸泡在浩瀚文字的福尔马林里。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女作家,波伏娃的标本意义在于,“她不但出版了她所能保存的、获得的全部信件,她还给萨特写了口述整理的传记,自己又写了四本厚厚的自传”。波伏娃用巨量的文字保持了她一生的原貌,“借以提供作为展览、示范、教育、鉴定、考证及其他各种研究之用”。
很难想象假如萨特和波伏娃之间有一纸婚书,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该如何维持。“整整一个时代都在谈论波伏娃和萨特这对恋人,他们给这半个世纪留下了一种态度、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存哲学”,他们都成了自己想成为的人:伟大的作家和哲学家。萨特并不认同一夫一妻制,他说:“在我们之间存在着无可取代的爱情,但是我们各自也会有些偶然发生的爱情。”波伏娃认同这种爱情,但她后来遇到的很多男人无法接受自己只是一段“偶然爱情”,她的美国情人艾格林就是如此。
大约是读《越洋情书》的先入为主,我非常喜欢书中那个柔软美丽的波伏娃,她深爱着自己的美国情人,但又不愿放弃和萨特的伙伴关系。她的矛盾、多情、才华和坚定在信中显露无遗,而在飞行技术尚不先进的年代,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越洋相会总是充满了艰辛和危险。和美国作家艾格林的爱情是波伏娃感情生活里特别重要的一段,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不想结婚的女人碰到了一个特别想结婚的男人。“波伏娃和萨特都不想破坏彼此之间融洽的关系,事业对他们来说才是最为重要的。但是偶然的机会,他们俩都爱上了想要结婚的人。波伏娃后来曾力图建立一种跨越大西洋的关系,以调和她对萨特才智的喜爱和对尼尔森·艾格林的爱情这两者间的矛盾”。1947年,39岁的波伏娃与39岁的艾格林在纽约因电话结缘。艾格林是个高大英俊的男人,刚刚离婚,和萨特矮小的形象截然不同。而波伏娃自己承认,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她和萨特就已经没有了性关系。艾格林和波伏娃恋爱之后希望能和她结婚,但是他完全搞不定这个女人,后来他和前妻复婚,又再离婚。这个两度结婚两度离婚的男人和波伏娃保持了多年的通信关系。波伏娃的小说《达官贵人》讲述的就是自己和艾格林的爱情,“她把这份不愿意自我消亡的爱情转变成文学作品,才终于得到了解脱”。但这本书的出版却让艾格林大发雷霆:“天哪,她是不是记下了我们做爱时的全部细节?”
萨特一生中说过多次,波伏娃身上最奇特的就是她有着男人的智慧和女人的多愁善感,她是情人又是朋友,更是终身伴侣。在他们两人一生的关系中,经常出现“三重奏”和“四重奏”。波伏娃和艾格林恋爱期间,萨特也有一段和美国女演员的爱情,这算是“四重奏”,另外一段著名的“三重奏”则被波伏娃写成了小说《女宾》。坦率地说,我喜欢那个写哲学著作《第二性》的波伏娃,不那么喜欢写小说《女宾》的波伏娃。奥尔加是波伏娃的学生,后来成了萨特的情人,和萨特及波伏娃组成了三人组合。萨特非常喜欢奥尔加,而奥尔加则爱波伏娃胜过爱萨特。这段三人关系当然没能持续到底,奥尔加后来和博斯特结婚,“三人奏”变成了“四人奏”,四个人关系良好。博斯特成了波伏娃的情人,关系长达十年之久,直到她遇到艾格林才中断。我认为波伏娃有着惊人的情商,这个一生不结婚的女人,在萨特这个终身伴侣之外有无数情人,她既能做到不和想结婚的男人结婚,又能做到不让不想离婚的男人离婚。波伏娃还能让很多女性爱上自己,虽然她在回忆录里一直否认自己是双性恋者,令人惊奇的是,“每当有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对波伏娃产生了爱慕之情,萨特就会想着追求这个女孩,不征服她决不罢休”。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展示了女性的性欲是何等复杂,“而多亏了她和萨特的关系,她也观察到男性性欲的复杂性”。
波伏娃一生中最后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发生在她44岁时,“波伏娃和一个小她17岁的伙伴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似乎是这个年纪的男人才有的特权”。波伏娃一直和萨特分居,也拒绝和艾格林生活在一起,但是她决定和她的小情人克洛德·朗兹曼生活在一起,让他住进了自己的公寓,过起了同居生活。他们共同度过了六年的快乐生活,直到小情人选择离开。后来,萨特爱上了克洛德·朗兹曼的妹妹埃弗利·雷伊,她同自己的哥哥一样,在政治上极端“左”倾,“在萨特的几段爱情中,这是陷得最深的一段”。是的,你没有看错,萨特和波伏娃可以和一对夫妻“四重奏”,也可以和一对兄妹“四重奏”。男女感情的各种可能与不可能,他们都统统体验过了。世上再也没有比波伏娃更像标本的女人了。
波伏娃骨子里非常浪漫,她堪称“用身体写作”的鼻祖。“她出版了自己的全部生活”,除了哲学著作《第二性》,她绝大多数的小说都是根据自己的生活改编的,比如《女宾》,比如《达官贵人》。《达官贵人》一书在中国还有一个译名为《名士风流》,这本书让波伏娃获得了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并因此得到了大笔收益:奖金和书的热销。她用这笔钱买了一间艺术家工作室,在那里一直住到逝世。因为和萨特之间没有一纸婚书,他们之间的财产关系也简单而复杂。其实,现代婚姻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感情关系,还是一种财产关系,没有婚书最终让波伏娃失去了对萨特遗产的继承权。波伏娃因为外祖父的破产,很小的时候就明白自己将来不可能有一笔体面的嫁妆,她一生独立,自力更生。萨特则为人慷慨,出手大方,当年他获得诺贝尔奖时,波伏娃曾劝他去领奖,因为当时他们正缺钱花。但萨特不接受一切来自官方的奖项。
萨特比波伏娃大三岁,他们可以说“识于微时”,最终相伴了五十年。“一生中,他们每年都会给自己安排几个星期的时间单独相处,这些时间通常都是在国外度过。”作为著名人士,他们还经常共同出访,由于他们左翼的政治观点,他们到访过古巴、中国、苏联等国家。作为女权主义者,波伏娃期望社会主义可以为妇女带来公平与平等。当波伏娃和萨特进入晚年时,他们都没有儿女。后来他们分别有了一个养女,各自组成了一个家庭,两个年轻女人陪伴他们度过了最后的岁月。萨特的养女其实是他的情人,波伏娃同养女之间也关系暧昧,但她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双性恋者。萨特曾经想同养女结婚,以便让她获得法国身份,但遭到了波伏娃的强烈反对,后来这个女孩还是通过被萨特收养的方式获得了法国国籍。这意味着养女将继承萨特全部著作权和遗产。波伏娃最终没有得到萨特的任何一样东西留作纪念。
“波伏娃/萨特组合的实质是:思想高于爱情”,正因为如此,波伏娃并不认为她和萨特之间形成的情侣关系可以作为榜样来效仿。波伏娃作为一个标本的意义也在于此:她是独一无二的,可以用来研究,但无法复制。波伏娃的身份不是萨特的助手和追随者,“她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她写出了她作为一个杰出的职业妇女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现代社会里的思想观念、感受体验、精神优越与矛盾苦闷、欢乐与幽怨”。选择成为一个标本,她首先具有智慧的头脑和强大的内心,无惧世俗世界的任何目光。
波伏娃说,写作一直都是我生命中的头等大事。我喜欢作为哲学家和女权主义者的波伏娃,喜欢她的那句名言:我们并非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后天变成的。波伏娃向我们展示了女人的一切可能,愿每个女人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人生。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