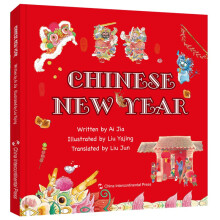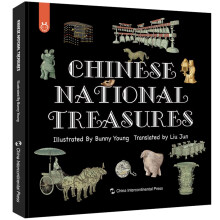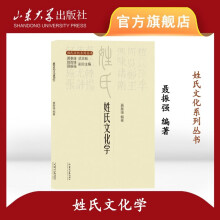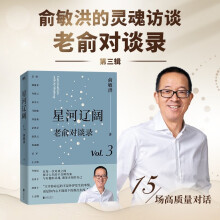《良善家风惠久远:优良家风家教故事文集》:
母亲的“钱”“情"观
我的母亲虽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却在村里有着超乎常人的好人缘。她离开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乡亲们想起她、提到她,仍有着一种敬重之情。年轻时我理解不深,直至走上纪检监察岗位后,才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是母亲的付出、母亲的“清廉”、母亲的“职业操守”,换取了乡亲们的敬重。
母亲没有任何职务,却有着一门独特的手艺——接生,是我们大队四个自然村唯一的接生员。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村子离公社卫生院较远,乡亲们的健康意识又弱,孕妇们临盆时,很少有人上医院生产,大多是请母亲到家里去接生,而母亲也总是随叫随到。
生孩子是不分白天黑夜、天气好坏的,母亲也只能不分白天黑夜、风霜雨雪地东奔西走。遇上顺利的,两三个小时孩子降生,母亲便算完成任务;遇上不顺利的,母亲只得一边帮助人家做辅产措施,一边与产妇家人一起焦急地等待,等上一昼夜,才听到婴儿啼哭的事儿,也是经常发生的。
因为帮人家接生,母亲身心疲惫,还耽误了家里的活计。产妇家人就有些过意不去,寻思着如何感谢一下母亲。母亲却坚守着自己的底线:人家送条毛巾,意思是因接生弄脏了手,赠条新毛巾擦洗一下,那就收下;送来点鸡蛋和红糖,母亲就过两天以到家回访、慰问产妇的名义还回去;有家境好些的想送母亲几块钱的辛苦费,母亲坚决婉拒。
在母亲的心里,她是真心地把自己的手艺当成一种职业来看的,以为社员们服务为己任的,所以她一直恪守着自己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绝不在乡亲们遇到难处时吃拿卡要,不发“急难财”,不挣“昧心钱”。母亲也确实做到了。
1971年腊月的一个风雪天,天将落黑儿时,一个离我们村三里多远的常桥村的张姓农家汉子急匆匆来到我家,说他老婆“到时候了”,邀请母亲随他到家去接生。
刚进厨屋准备烧锅做饭的母亲一听,立马转身回到堂屋,一边收拾产包,一边安排我:“去后院把你奶奶请过来,让她照顾着你和弟弟。天快黑了,还下着雪,又有那么远的路,我得赶紧走。”于是,刚满七岁的我,只得跑到奶奶家里,搀着她老人家冒雪过来照看只有一岁的弟弟。
我们进家时,母亲他们正好出门。张姓汉子见到奶奶,略显歉意地忙上前去扶住奶奶,嘴里念叨着:“大娘,对不住,又要麻烦大姐了!”母亲也上前迎住说:“妈,我得赶紧去常桥。”奶奶已习以为常:“去吧,去吧,小孩饿了我给他热羊奶喝。”看着母亲顶风冒雪逐渐远去的身影,我有些担心,便对奶奶说:“妈妈不害怕吗?”奶奶轻轻地拍拍我的头,温和地说:“你妈是个好人,她是在行善积德,不怕。”
两天后,母亲才满身疲惫地回来。后来才知道,张家这产妇胎位不正,是母亲用尽办法为她矫正了胎位,才使得母子平安。
又过了几天,那张姓汉子又来我家,这次是专门答谢母亲的。他送来了十块钱,说母亲“救了他家两条命,按理说这十块钱太少,拿不出手”,并请求母亲不要嫌弃。母亲坚辞不受,却话如春风:“谁家挣钱都不容易,兄弟也不必客气。你叫我一声大姐,说明咱们都不是远人,说钱实在太外气了。再说我干这活就是为乡亲们服务的,不是用来挣钱的!”那汉子钱没送掉,却含着两眼热泪去了。
我看着这情形十分不解,对母亲说:“不是正发愁没钱买肉过年吗?人给钱咋不要啊?”母亲盯住我一会儿,缓缓地说:“孩子,老话说,自己吃了填坑,人家吃了传名。你看那是钱,我看那是情。不收钱那情就在,收了钱就等于把情卖了啊!”看我有点似懂非懂,母亲继续说:“你现在还小,可能还不太明白,但你只要记住这话,长大了就用着啦!”我看着母亲庄重的神情,只得点了点头,并用心记下了这话。
待到我长大成人,走进军营,走上社会,我才逐步体会到母亲那“钱”与“情”的论断是何等的高妙!虽然现在乡亲们回忆起这些事,还在替母亲“惋惜”,说那可是独门手艺,如果想挣钱可比现在开诊所的容易得多;虽然由于母亲的“经济意识”淡薄,没能为家里积攒一定的物质财富,以致我们兄弟姐妹没有享受到新衣美食;虽然母亲拒收的钱、收获的情并没有得到惊天动地的回报,但在母亲1992年10月溘然长逝时,我却见到了乡亲们那浓浓的友善和情义——满村举哀、万人空巷送母亲!年轻人人人争先抬棺,年迈者个个痛哭失声。几个同辈至今忆起那场葬礼,仍对我说:“那棺材恁大,走得那个平稳啊,再没见过……”
是啊,母亲把“钱”和“情”分得那么清楚,本就没有图什么回报,恐怕唯一所图的,就是生前积善、走时坦然吧!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