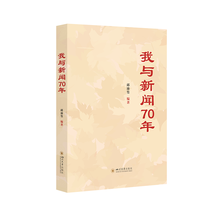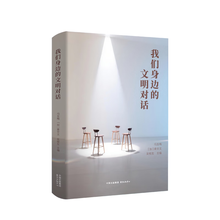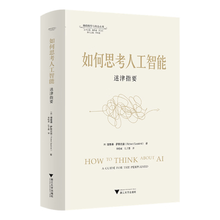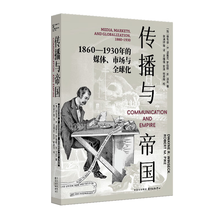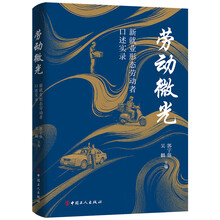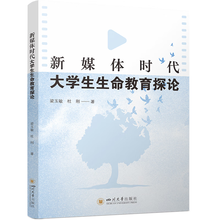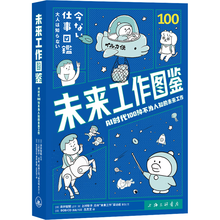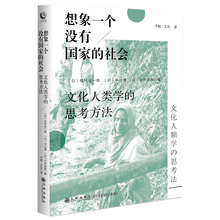《听涛文稿》:
方寸者,心也。心不正则眸子吒,看人带偏见,开口说鬼话,办事尽捣蛋,此“人即为鬼”之鬼也。如嫉贤妒能,搬弄是非,见风使舵,吹牛拍马,……阳间确不乏其人。钟馗就是遭此“鬼”打过。所以他慨然受命,接过花名册,怒目圆睁,咬碎钢牙,“打”得非常卖劲。
小说家言,总是不乏穿凿附会,生发人事。这说明钟馗形象的艺术价值非同小可。钟馗的形象主要表现形式是绘画,从吴道子作画张贴千家万户,钟馗的形象就广为人知。主要是水墨画,也有瓷画、木刻(拓片)、石刻、石雕、泥塑、陶塑、剪纸……有钟馗出游、钟馗嫁妹、钟馗骑鬼、寒林钟馗、钟馗杀鬼、钟馗读书、钟馗搔背……不管姿势服饰、故事情节怎么变化,其相貌的丑陋,疾恶如仇的心理,几乎是一致的。虬髯惊目,佩剑执笏,袒胸露臂,威风凛凛,鬼见胆寒。而不第的身世,令他疾恶如仇,使这个驱鬼大神的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在文艺作品中,貌丑而善良的形象所产生的艺术力量,是很有征服力的。如《巴黎圣母院》中的夸西莫多,相貌其丑无比,而内心的善良之光,却照亮了千千万万人的心灵。又如京剧艺术中的黑脸包公、花脸张飞以及《白蛇传》中的白蛇精青蛇精等等,善良美好的故事,通过这些怪异丑陋的外形来表现,往往产生奇特深沉的艺术力量。由此可见,艺术的力量,存在于个性之中。
钟馗的“职责”是打鬼,在各种艺术作品中,打法也不尽相同。执剑斩鬼的,罚鬼干活的,挖鬼的眼珠子放进嘴里嚼的,命鬼倒酒给他喝的……招数很多。惟刳目而食(挖眼珠子吃)显得最解恨。吴道子的画作中,钟馗是以食指抠鬼的眼珠子,几百年后,蜀后主王衍认为用右手食指刳目,不如改用拇指更有力一些,于是要画家黄筌将吴道子的画改一下。黄筌觉得随便改动一个手指头,与原作的气韵神态不合,只好重新画一幅,把钟馗用食指抠鬼的眼珠子改为用拇指挖进鬼的眼眶,抠出眼珠子。这样一改,更能表现钟馗的疾恶如仇。而吴道子的原作并未改动,这样两个版本各有千秋,互为轩轾,流传于世。
十年前,我在湖南酃县文物所见到一块刻有钟馗画像的石碑,阴阳两面形象不同,阳面为文像,阴面是武像;阳指钟馗活着的时候是个秀才,阴为钟馗死后成了驱魔大将军。阳面为阳刻,阴面为阴刻,大抵为了拓片也有阴阳效果。遗憾的是,阳面在“文革”中被一农民用锄头挖坏,文像已无法得见。阴面的武像保存尚好,魁梧无比,骑一怪兽,像是麒麟,手持宝剑,双目如炬,栩栩如生。石碑曾被用来铺路,被当地一村民发现,才由县文物所收藏起来。碑的上方正中留有一方空白,据说古代凡在酃县当过县令的官员,退休时总要拓一张钟馗画像,钤上酃县县府的大印,揣在身边,以明驱鬼之志。这个习俗一直到民国初期还在沿袭,很可能与钟馗在酃县做过县令的传说有关,石碑上方中央的空白,大抵给钤县府大印预留的吧。
2005年10月16日
附记:此文初稿最早见于1986年2月23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记得当年光明日报登出后不久,收到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周定一先生赐函,予以鼓励,我很感动。周定一先生是大学者,语言学家,也是我的湖南同乡,对钟馗石刻发现在湖南酃县,很感兴趣,并就钟馗故事与我探讨。现将周定一先生两件来函附后,以飨读者。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