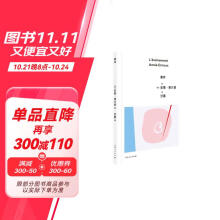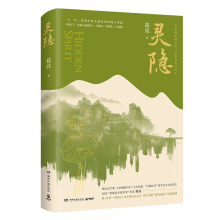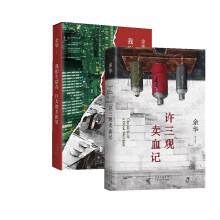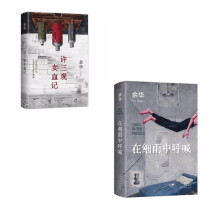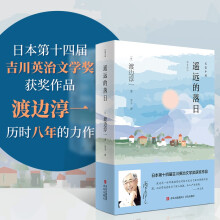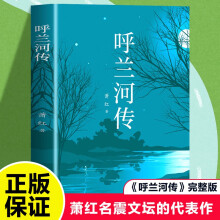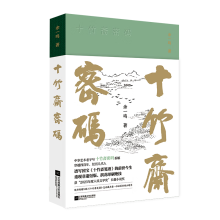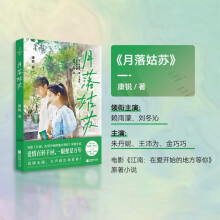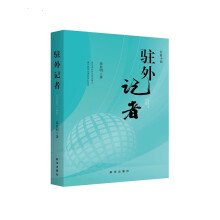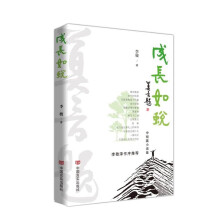莫莉·莱恩的两个老情人站在火葬场礼拜堂的外头候着,背对着二月里的凛寒。该说的全都说过了,不过他们俩又重复了一遍。
“她一直都不知道是什么要了她的命。”
“知道的时候为时已晚。”
“真是病来如山倒啊。”
“可怜的莫莉。”
“呣。”
可怜的莫莉。事情开始于她在多尔切斯特烧烤店外扬手叫出租车时胳膊上的一阵麻痛;然后这种感觉就再也没有消失过。几个星期之内,她就已经记不大清很多事物的名字了。议会、化学、螺旋桨,忘了倒也罢了,可是连床、奶油和镜子都记不得,她可就不能原谅自己了。她是在一下子想不起叶形装饰和风干牛肉干的名号以后才去就医的,本来期望医生说没什么大不了的,谁知却被送去查了又查,感觉上像是永远都查不完了。于是一转眼间,性情活跃的莫莉就成了她那位脾气乖张、占有欲极强的丈夫乔治的病室囚徒。莫莉是美食评论家、既睿智又迷人,又身兼摄影师和敢于创新的园艺家,连外相都爱过她,四十六岁上还翻得出完美的侧手翻。她堕入疯癫和痛苦的速度成了坊间八卦的谈资:先是身体的机能失去控制、幽默感随之全盘尽失,然后就是渐渐意识模糊,间以徒然的暴力挣扎和被人捂住嘴巴的痛苦嚎叫。
看到乔治的身影从礼拜堂里出来,莫莉的两个老情人退往杂草丛生的砾石小径。两人踏进一处椭圆形的玫瑰花床,花床边上树了块牌子,叫“追思花园”。每一株花茎都惨遭砍戮,距冰冻的地面只余几英寸高,莫莉生前对此种做法是深恶痛绝。小块草坪上遍布踩扁了的烟头,因为人们就是在这里等着前一拨参加追悼会的人群离场的。两位老朋友来回踱步的辰光,再次捡起之前已经以各种方式讨论过五六次的话题,因为这可比一起唱《朝圣之路》更让他们觉得安慰。
克利夫·林雷认识莫莉在先,早在六八年他们还是学生的时候,当时两人一起在“健康谷”同居,不断地搬来搬去,情形真是混乱不堪。
“走的方式实在可怕。”
他注视着自己呼出来的白气飘散入灰色的空气。今天伦敦中心地区的气温据说降到了零下十一度。零下十一度。这个世界真是出了大问题了,而为此既不能责怪上帝的存在也不能归罪于上帝的缺位。人类的第一次违抗圣命,人类的堕落,一个下行音型,双簧管,奏出九个、十个音符。克利夫对于音高的判定具有绝佳的天赋,听着它们从G调依次下行。根本就无需记谱。
他继续道,“我是说她死的方式,这么无知无识,就像动物。就这么衰竭下去,受尽屈辱,根本来不及安排后事,甚至来不及说声再见。疾病就这么悄悄上了身,然后……”
他耸耸肩膀。两人走到了备受践踏的草坪尽头,掉头再往回走。
“她宁可自杀也不愿落得如此下场,”弗农·哈利戴说。他七四年曾经跟她在巴黎住过一年,当时他在路透社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莫莉则为《时尚》杂志干点杂活。
“脑死亡,而且还处在乔治的魔爪之下,”克利夫道。
乔治这位可悲、富有的出版商对她是百般宠爱,尽管她对他一直都颐指气使,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并没有离开他。他们俩看见乔治正站在礼拜堂门外,接受一群哀悼者的慰问。她的死倒是抬高了他,不再受到众人的鄙夷。他看上去像是长高了一两英寸,后背挺直了,声音也低沉了,一种新生的尊严把他那原本求肯、贪婪的眼睛都收窄了。他拒绝将她送往疗养院,而是亲手来照顾她。更有甚者,在早先大家还想探望她的时候,都要通过他的审查。克利夫和弗农受到严格限制,因为他们被认为在见面时容易使她兴奋,见面后又会使她对自己的病情悲观绝望。另一位关键的男性外相大人,同样也被列入黑名单。大家开始议论纷纷,有几个闲话专栏还不指名道姓地进行过影射。再后来也就无所谓了,因为传出消息说她已经绝非昔日的莫莉;大家也都不再想去看她,倒是很高兴乔治充当了挡箭牌。不过,克利夫和弗农则一如既往地以憎恶他为乐。
他们再次折返时,弗农兜里的手机响了。他道声歉后退到一边去接电话,留下他的朋友独自前行。克利夫紧了紧大衣,放慢脚步。现在,身穿黑衣挤在礼拜堂外面的足有两百多号人了。再耽搁着不走过去跟乔治说点什么就显得很无礼了。他终究还是得到了她,在她连镜子里自己的脸都不认识的时候。他对于她的风流韵事束手无策,可到了最后她还是完完全全属于了他。克利夫的双脚都快冻木了,跺脚的节奏又使他想起那十个音符的下行音型,渐慢,英国管柔和地扬起,与大提琴形成对位,宛若镜中映像。她的脸也在其中。大结局。现在他只想回到温暖、寂静的工作室,回到钢琴和未完成的乐谱旁,把乐谱写完。他听到弗农在结束通话,“好的。重写导言,放第四版。我一两个小时后到。”然后他对克利夫道,“该死的以色列人。咱们该溜达过去了吧。”
“我想是的。”
可是两个人却又围着草坪转了一圈,因为他们毕竟是为埋葬莫莉来的。
弗农努力集中精神,排除办公室的糟心事儿。“她可真是个可人儿。还记得台球桌上那一幕吧。”
一九七八年,一帮朋友在苏格兰租了幢大房子过圣诞。莫莉当时交往的是个叫布兰迪的王室法律顾问,两个人在一张废弃的台球桌上表演亚当和夏娃的活人造型,他只穿了条小紧身内裤,她只剩下胸罩和内裤,一个球杆托儿当那条蛇,一个红球当苹果。可是这故事以讹传讹之后的结果,出现在一个讣告当中就成了莫莉“曾于某平安夜在某苏格兰城堡的台球桌上全裸跳舞”了,即便当时在场的有些人的记忆也被修订成了这样。
“是个可人儿,”克利夫赞同道。
她当时假装去咬那个苹果的时候曾直直地望着他,咬得咯咯响的牙齿间露出淫猥的微笑,一只手支在撅起来的屁股上,就像杂耍戏院里戏仿的妓女形象。他认为她接收他眼神的方式是个信号,果不其然,他们俩在那年四月再度复合。她搬到他南肯辛顿的工作室,度过了整个夏天。当时大约正是她写的餐馆评论专栏刚起步的阶段,跑到电视上公然抨击《米其林指南》是“美食上的媚俗”。也正逢他自己的事业首度时来运转之际,他的《管弦乐变奏曲》在皇家节日音乐厅上演。破镜重圆。她或许并没有什么改变,不过他已经不再是昔日的他了。十年的光阴没有虚掷,他已经学得了些经验,放手让莫莉来引导他。不论干什么,他一直是全力以赴的。她教他偷潜性爱的技巧,也就是偶尔要静止不动。一动不动地躺好,就像这样,看着我,认认真真地看着我。我们就是定时炸弹。他当时快三十了,照今天的标准算大器晚成的了。当莫莉找好自己的住处要打包走人时,他求她嫁给他。她吻了吻他,在他的耳边悄声引述:“他娶一个女人是为防她离他而去/如今她却整天赖着不肯走了。”她是对的,因为自她走后,独处的滋味快乐无比,不到一个月时间他又写出了《秋歌三曲》。
“你可曾从她身上学到过什么东西?”克利夫突然问道。
八十年代中期,弗农也跟她来了个梅开二度,那是在翁布里亚的一幢度假屋。当时他是如今他主编的这份报纸的驻罗马记者,已经成家立业。
“性爱的事儿我总是记不住,”他踌躇了一会儿道。“我肯定应该是非常棒。不过我的确记得她教我认识牛肝菌,怎么采摘,怎么烹饪。”
克利夫认为这是虚晃一枪,决定不再跟他推心置腹。他朝礼拜堂的门口张了张。他们是该进去了。他突然溜出一句相当残忍的话,把自己都吓了一跳,“你知道,我真该娶了她。在她开始昏迷的时候就拿个枕头什么的闷死她,免得大家都来可怜她。”
弗农呵呵笑着引他的朋友离开“追思花园”。“说说容易。我可以想见你在放风的院子里给犯人们写颂歌呢,就像那个谁,那个搞妇女参政运动的女人。”
“伊瑟尔·斯密斯。我铁定比她要写得好。”
参加葬礼的莫莉的朋友们并不想跑到火葬场里来,可乔治摆明了不想搞任何追思仪式。他可不想听老婆的三位老情人公开在圣马丁或圣詹姆斯教堂的讲道台上交换什么意见,或者在他本人致悼词时在底下挤眉弄眼。克利夫和弗农进门之际,听到的是鸡尾酒会上熟悉的嗡鸣。没有香槟酒托盘,也没有饭店里幕墙的回声,不过除此以外跟画展的开幕或是媒体投放会也没什么两样。有那么多面孔是克利夫从来没有在日光底下照过面的,看起来可真是恐怖,活像是僵尸直立起来欢迎刚死的新鬼。一阵愤世嫉俗的情绪发作之下,他迅速穿过那一阵嘈杂,有人叫他的名字他也不理,有人拽他的胳膊他干脆甩脱,继续朝乔治站立的位置走去,乔治正跟两个女人和一个呢帽手杖的干瘪老头儿说话。
“太冷了,我们得走了,”克利夫听到有个声音叫道,但此时此刻谁都甭想挣脱社交场合的向心力。他已经把弗农给丢了,弗农被某个电视频道的老板给拉到了一边。
最后,克利夫以适度的诚恳态度握住了乔治的手。“告别仪式非常出色。”
“非常感谢您的到来。”
她的死使他高贵了起来。那种静静的庄严绝非乔治平素的风格,他一贯既阴郁冷酷又索求无度;既急于求得他人的喜欢,又不能将友谊视作理所应当。这是巨富们才有的一种负担。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