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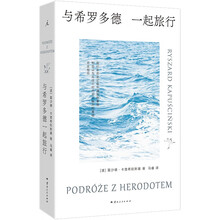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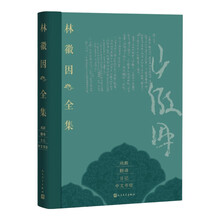
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得主任林举、“赵超构新闻奖一等奖”得主孙翠翠*新力作,为您讲述吉林水稻的前世今生。
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得主任林举和资深记者孙翠翠,在大米供求处于紧平衡状态,食品质量安全备受关注的背景下,历时两年,深入田间地头和基层粮企,采访了上百位农民和粮食企业家,以及各级粮食管理部门和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全国四十多名水稻专家,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创作《贡米》,完成一个“为农民、为土地、为粮食安全做一点事儿”的夙愿。
后 土 无 言
一
古朴的小村静静地躺在9月的晨曦里。
潋滟的阳光如某种带有甜度的油彩,自那火轮般旭日升起的东方,源源不断地流泻出来,将大地与天空、农田与河流、树木与房屋统统涂上梦幻的色彩。小村的名字就叫“南坊”。这个距榆树县城25千米、距大坡乡仅仅3千米的小村,似乎没有人能够说得清它名字的由来和村子的发展、变迁史。也许很久以前就有人在这里建坊安居,也许从前这里不过是一片荒原。但如今看起来,它却如百年以前、千年以前、万年以前就一直坐落在那里一样,安稳中透露出地老天荒的况味。有那么一个时刻,你甚至会以为它与永恒的时间同在,从来都是那个样子,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
八十三岁的孙令山老人冷不丁推开自家的房门,给小村静谧的早晨制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惊扰。“咣当”一声关门声响起,仿佛整个睡意未消的清晨都跟着颤抖了一下。声音的波纹以老人站立的地方为原点,荡漾着,一波波传向远方。一只黑色的猫,披着一身残留的夜色,从对面的墙头跳下来,梦游似的,向孙令山老人走来,几步之后又折返身,踱至相反的方向。一只早起的白鹅,不走,也不叫,只是默默地伸长脖子,站在孙令山的对面,一会儿把头侧向左,一会儿又把头侧向右,好像有一个十分难懂的问题,正困扰着它,让它百思不得其解。院前唯一一棵海棠树上,没有鸟儿,也没有果子,枝头挂满了紫红色的树叶。想来,树真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它们不用走,也不用挪,就能和人一样走过春夏秋冬,走过许许多多的岁月。多年后,有的人老了,它们却不老;有的人不在了,它们却依然健在。它们不声不响,却能准确无误地感知季节的冷暖炎凉,能够以形态和颜色的变化表达出自己的际遇和情绪。但树的心思我一直不是很懂,比如这个早晨,那棵树上的叶子透出的红,到底是晨曦的颜色、冰霜的颜色,还是岁月的颜色?孙令山出门后,半晌没有动身,就那么久久地望着眼前的树发呆。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就是大半个世纪。生活中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而孙令山在这个世界的姿态却始终保持着不变。他每天都是这样,早早地从炕上爬起来,天未亮,脑子里还在回放着梦里的事情,就一头扎进田里。梦里的事情,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很不好的,但这对孙令山来说都无所谓,因为梦里的事情不管是好是坏他自己都说了不算。他心里清楚,他真正能说了算的只有一样,那就是他自己的田里能长出什么。所以,他只有到了田里,一颗心才真正踏实下来。他愿意把心中的那些想法,哪怕是难以实现的美梦,都交给土地。凭着大半生的经验和阅历,他坚信只有土地能够不打折扣地信守承诺,只有土地才是他许许多多个梦里最听安排的一个。如今,他已经上了年纪,田里的事情都由子女们接手。已经有一些年头他不必每天急匆匆往田里跑了,但每天的这个时候,依旧按时起身,转转悠悠就到了田间。有时,就算真的不用再去田里,他也要早早地起来,站在门口巴望着自己的日子,巴望着自己近处或远处的田地和庄稼,仿佛这一切只要他“一眼照顾不到”,就会像那些不靠谱的梦境一样消散得无影无踪。
先前,孙令山的家并不在南坊。据长辈人讲,他家是在清末荒年随大批饥民从山东“闯关东”来到东北的。到东北的第一个落脚点也不是吉林的榆树,至于确切的迁徙路线和其间的种种波折,早已在人们断断续续的讲述中变得支离破碎、模糊不清。想来,那也是一场不堪回首的逃亡,既然不是什么光荣历史,不提或少提也罢。沿途走走停停之间,这个家族似乎曾经有过四五个短暂的居留之所。直到南坊村的前一站,那个很久以前叫作“三棵树”的地方,才算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落脚点”。那是哪一年的事情呢?反正,那时孙令山还没有出生。孙家人本以为到了关外就到了幸福、甘甜之乡,没想到荒年就像一个不肯罢手的仇家一样,跟在他们身后穷追猛打,如影随形——天不作美,地不留人。他爷爷只好把一个八口之家放在一挂破旧的马车之上,一程接一程地走在迁徙的路上。
大平原一望无际,渺无人烟。一干饥民、一匹瘦马,就那么摇摇晃晃、踉踉跄跄地前行。迷茫,无望,满眼都是干裂的土地和瘦弱的枯草,没有一点点启示和参照,偌大的世界哪里才是安身立命之处呢?某天正午,正当这一干流民魂魄欲断的时候,一抬头突然看见了三棵榆树。树上有鸟,树下有丰茂的草,不远处的低洼地带传来隐约的流水声……孙令山的爷爷顺手拔掉一棵蒿草,抓一把根系下的泥土。一把黝黑黝黑、润泽、肥沃的泥土,立即让这位积年累月在饥饿里流浪的一家之长流下了泪水。这就是传说中“攥一把能流油”的黑土吗?全家人立即意识到了命运的暗示和眷顾,但却没有意识到,自己脚下这片土地正是上天赐予人类的“米粮之仓”。在这命运的阴凉之地,他们留了下来,并起誓“打死都不会离开”。这天赐的土地、未来的家园,应该怎样命名呢?因为有了近于“神示”的三棵榆树,一切才得以确立,那就叫“三棵树”吧!
孙令山的记忆是在九岁时逐渐清晰起来的。那时,他所在的村庄就已经叫南坊村了。至于土地上的人群是怎么变得越来越大的,家园是怎么变得越来越小的,传说是怎样变成现实的,很久以前的“三棵树”又是怎样演变成南坊村的,他已经在记忆里梳理很多次,但始终勾勒不出一个清晰的轮廓。对孙令山这样的北方农民来说,不管生活或生命里发生了什么,都只能老实面对。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知就是知,不知就是不知。他们最深恶痛绝的就是无中生有、牵强附会,所以面对类似的追问,他只能三缄其口,漠然以对。
孙令山扛起铁锹,迈动双腿向田间走去。他的步履轻盈、有力。不论从哪个角度,都看不出一点儿老迈之气,好像连岁月也被他甩到了身后,此时正呆呆地停留在门口,以一种惊奇的眼神看着他独自走远。这些年,南坊村的田已不再是从前的田。从前,每家每户或生产队的地,都要与房舍拉开一段距离,而现在,土地越来越金贵,寸土寸金,人们都把水稻种到了家门口。房前、屋后、沟塘、洼地到处是水稻。过去,田地隶属于村庄,现在,村庄隶属于田地。孙令山走过村子最东头的鲁家时,正好遇到这家出来倒灶灰的媳妇。对这个睡眼惺忪的村妇,孙令山只是简单地打个招呼,目光一扫而过,甚至连一秒钟都没有停留。八十三岁的孙令山虽然也知道自己的状态已经非二三十年前可比,但自觉还是一个男人而并非一个单纯意义的老人。对一些瓜田李下的事情,他还是保持着一贯的态度,谨慎回避,更何况,眼下村子里的精壮男人和年轻一代大部分都离开村庄到城里去打工或求学了。但今天早晨孙令山却一改常态地回过了头,因为那妇女从身后问了一个他不知怎么回答也很不舒服的问题。她问他,这个时候扛着一把锹去做什么?这是阳历的9月下旬,中秋刚过,田里的水已经放尽,节气一天天逼近开镰的日子,可是他扛着一把铁锹去干什么呢?这个问题、这把不合时宜的锹,像一道无形的“障子”,把他死死卡在了一个尴尬的处境。
很多年以来,除了要干应季的农活儿,没事时孙令山的肩上随时都扛着一把铁锹。锹在他手里就像啄木鸟的嘴一样锐利而灵活,可以疏松板结的土地,可以挖去多余的草根、树根,可以剔除田里的树枝、石子,也可以随时修复残破的田埂……一个人、一把锹,随时让土地保持着良好的状态。他觉得,这样好的土地,只有他这样的人才配拥有和守护。
然而,今天这个早晨,面对着丰收在望的田野,他竟然感觉到难以言表的惆怅。久久徘徊在大片大片的稻田之间,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也不知道哪一块田、哪一方土属于自己。合作社、大机械、大规模机械化作业、大面积深度整饬、标准化规模化发展……很多的大词儿他都不明白确切的含义,但这些词合到一起已经产生一种无形的力量,把他和他的土地分隔开来。他满心郁闷,却找不到一个发泄口,似乎一切都是他并不讨厌甚至是有些折服的,可到头来却又像是一个骗局一样,把自己“绕”进一片没着没落的虚无里。他在田间空空落落地转了一会儿,想给肩上的这把铁锹派个什么用场,最后,他找了一个田埂外边的空白处深深地挖了下去。
锹的凹面在向下行进的过程中,与泥土产生了轻轻的摩擦,他那只踏着锹的脚,能够感觉到那种微微的震动。于是,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欢畅就从那铁刃与泥土交接处传导上来,通过木质的锹把、老茧未消的双手传遍全身。他并不急于将铁锹一踩到底,而是在大地对他脚下那块铁的容忍和力的纵容中,再一次感受、确认着自己和土地之间的关系。他将手腕一反,一锹黝黑的泥土就从大地上分离出来,在孙令山心里,这是世界上最美的物质。对这个土生土长的北方农民来说,他并不知道眼前这一锹黑土里含有什么营养成分,他只知道那土里饱含了生长的力量和上天的祝福。只要那捧松软、黝黑、油亮的土在他的眼前一晃,就意味着翠绿的庄稼、金黄的粮食和说不清是什么颜色的希望。
……
后土无言 010
黑土简史 020
“白浆土”之梦 027
来自地心深处 037
土生土长 049
大湖隐没 061
第二部?结水为瑶 071
自天而来的河流 072
水做的稻 080
寻“宝”的人 092
“吉粳88” 099
“吉粳511” 106
端稳政策的“竹竿” 110
“弱碱性”的契约 122
海兰江畔的“白衣民族” 134
水稻花开与鸭田 140
第三部?昔日“皇粮” 149
雕龙石碑 150
长春大米 155
“贡米”的故乡 161
优质米的秘密 180
“贡米”是一种品质 187
专家论稻 196
第四部?鞠养万方 213
危机四伏 214
“健康米”工程 221
“格格”转身 229
一切都在你的眼前 246
以最直接的方式 256
怎样你才相信 262
结?语 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