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姐和四姐都从被窝里伸出毛茸茸的头,朝窗外看,三姐探花“噢”一声一下子坐起来,开始很快地找她的棉袄棉裤,一边催四姐探果:“好大的雪噢,好大!”奶奶已经挽着胳膊端着高压锅进来,一股很浓的牛肉香味能勾出馋虫来,我便把手伸得老长,二姐一木梳打过来,把被子从我身上一掀,恶狠狠瞅我说:“起来吃。”我鼻子一酸,准备张开大嘴哭给奶奶听,或者妈妈。二姐突然朝窗外说:“果果,捏雪球好不好?”四姐探果说声“好”,扣着扣子下炕找鞋子穿。我蹦了起来,张着手往下跳,怕迟了撵不上她们。奶奶丢下锅逮住我,大姐帮着给我穿衣服,说:“哄你哩,饭还没吃,捏啥雪球。吃了饭去。”
三姐探花那声狼嗥一点儿算不上没见过世面,雪大得差点让我又吓尿裤子。走到屋门口,要不是门口半身高的旧砖院墙挡着,我会扑进雪窝里打几个滚儿、翻几个跟头。这堵院墙也只让我犹豫了不到眨两遍眼的工夫,就扑进雪窝里了。雪可真厚,埋到膝盖深,可还在下,像弹棉花的人得了失心疯,不要命地往外扔,扔得满世界都是。我倒在雪里打滚儿,咯咯咯地笑,要是大姐在,一准又说我笑得像老母鸡下蛋。“呸”,我吐了口唾沫。滚在雪窝里,仰脸看满天的雪,雪下我一脸,又笑。四姐探果袖手倚着门,看着我笑。三姐也跑出来了,一个劲儿跳脚,不停去雪里团雪球,然后扔给我,叫:“你也扔我,扔我。”二姐拿着一把小铲子,不笑,不跳,也不叫,已经在院门口堆成一个小小雪人,她这会儿正抓一把雪手里团着,准备安装鼻子,不成想一个雪球飞过来,雪人的脸打出一个坑来。二姐跑过来捉我,我挣扎着叫:“不是我,不是我。”十分无耻地把手指向三姐探花。二姐飞天转身去捉三姐探花,三姐探花身子一矮,从二姐飞天的鹰爪下逃脱。她们俩满院子追着跑,我猫着腰坏坏地笑着跟在后头打黑枪,不管打着谁,都当是对方干的。三姐便不停尖叫,不停张牙舞爪,一肘子顶到了我的头上。
在妈妈骂二姐和三姐的时候,雪停了,有个阿姨的声音从院门口传进屋:“哇斗,哇斗嫂子在家吗?哈哈哈……”妈妈马上迎出去,立刻就听到了妈妈笑着朝奶奶喊:“娘,你看谁看你来了,富贵家的,田来他娘。”奶奶笑着从屋里走出来,田来他娘嘎嘎笑着抓住了奶奶的手,叫着“大娘”一起进屋,我妈妈手里也牵着一个男孩,长得不黑,跟二姐差不多大小,跟我们说他是“来来哥”。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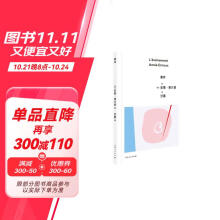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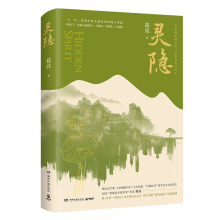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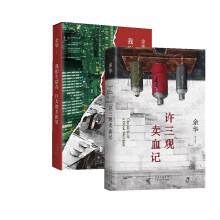







——著名文艺评论家、学者 张澄寰
王凤英的小说语言充满了诗性,使她笔下的人物更加鲜活灵动,作品更富有生命和灵魂的气韵。
——著名作家、鲁奖得主 温亚军
无论从其小说叙述能力的自在裕如,还是在作品中对道德人格的兀自标示,都透露出一股难以言传的优越和清高。她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君子之道、丈夫气概与当代军人的严格自律相对接,而且天衣无缝。
——著名文学评论家、诗人 殷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