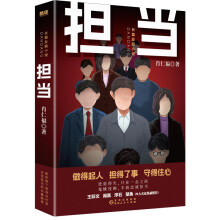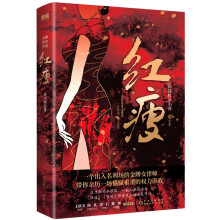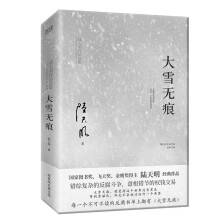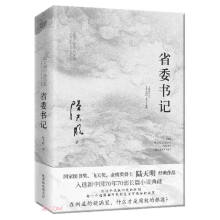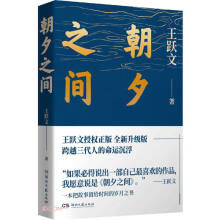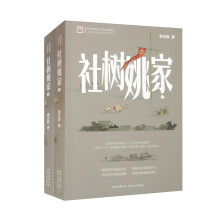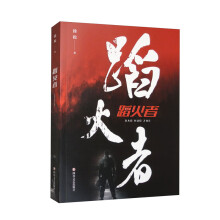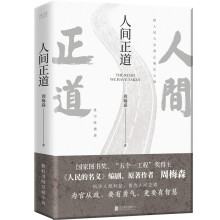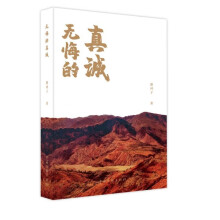龙门村里有一老一小两个羊倌儿,一到冬天,就戴上羊皮帽子,穿上肥大臃肿的羊皮袄。爷俩儿常年在崮顶上放羊,一般不下趟山。山下的人偶尔碰见到他们,忍不住想哈哈大笑。人们参照电影《林海雪原》里的土匪,给这一老一小都起了外号,小的叫“小炉匠”,老的叫“老炉匠”。
为此,王树义去问计于上一任书记。姜还是老的辣,老书记给他提供个信息:据此地二十多里的博城县,有个七里寺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出一个两个小皮匠。
一个区域,有一个区域的传统文化。说起制造大爆仗、小鞭炮,人们不约而同就会想到祝家庄;做年画的,印灶王爷、门神的,则是杏花村;打造砚台的,就是龙门西北的那个竹西村。当然,好长一段时期,有些题材的年画以及砚台等,几近绝迹。那些玩意儿,弥漫着浓郁的迷信色彩,属于“四旧”范畴,好长一段时间,没人敢鼓捣。祝家庄倒是还有人在做鞭炮,产量也很小。至于烟花,那时候更是极少极少,仅供市里、县里大型活动需要。普通老百姓家哪能买得起呀?
七里寺距离龙门,得有二十来里路。要是交通便利,这么一骨节路,倒也不远。可一者交通不行,再一个农村人口流动不频繁。别看区区一二十里山路,却分别属于两个县,这两头就变成两个封闭区域。人员之间,除丁走亲串友,互相往来的极少。更何况,在山里可用的交通工具,基本就靠两根腿。乘坐驴车、牛车,已经比较高级啦。可驴车、牛车属于大队集体,一般人家哪里有?想坐你也坐不上。
王树义挥着鞭子,赶着大队的驴车,前往七里寺。
驴车上,还坐着一位本家婶子。
这位婶子的娘家,便是七里寺的。饥饿年代,山旮旯里的日子比山外好过些。这位婶子当时还是没嫁人的姑娘,一路逃荒而来,到龙门村口,饿得实在走不动,身子摇晃几下,轰然躺倒在地。恰好,王树义一个没出五服(不是直系,但血缘关系比较近)的叔叔经过,把她背回家。没想到,让他爹他娘好一顿骂,让他从哪里捡的再送回哪里去。那时节,哪一家也没更多粮食呀,多一个大人,就多一张嘴,多一分艰难。这个叔叔,背着姑娘往家走的时候,兴许也不完全是怜悯之心,内心恐怕也有点儿小想法。因为,他年纪已大,还是条老光棍!撬开嘴巴,灌进一点点儿地瓜糊糊,姑娘好不容易醒过来,把脸一擦干净,咦?这叔叔顿时眼睛一亮:姑娘看上去挺俊呀!他爹他娘一瞧之下,对视一眼,也动起心思来。等姑娘身体恢复过来,他娘曲里拐弯一打听,姑娘是没定过亲的!于是,把话头挑明,姑娘也觉得,龙门这地方还不错的,外面连榆树皮都刮下来吃光啦,山里居然还有地瓜秧子可以填饱肚子。干脆留下不走,嫁给救他回家的男人,成就一段佳话。
多年过去,这家孩子还问她娘:“那么远,你咋跑到这山沟沟里来啦?”她娘只管笑,笑过后说:“还不是你爹,心眼子不好使!他把我硬扛到你家来的。”
在婶子引荐下,王树义跟七里寺大队李书记顺利接头,聊得很是尽兴。
“去,抓只小鸡儿炖上!”李书记好客,几句话过后,扭头咋呼老婆。
常年见不到肉的年月,能杀鸡来招待客人,算是相当热情啦!王树义虽然做过准备,提一粗陶罐子散酒去,可心里觉得还是不大好意思。
几盅子酒下去,李书记一拍大腿:“忘个事儿!我介绍个人给你认识认识。”扭头又喊老婆,“你去看看清泉走了没?他要没走,把他喊来,一块儿哈点儿酒!”
当地方言,管喝酒叫哈酒。
王树义没想到,这样一次机缘巧合,让他跟李清泉结识。
他更不可能想到,这个人,接下来将和他结缘大半生。他们会在一起摸爬滚打,一起喝酒,一起畅谈,一起共渡难关。
一直过去许多年,有一天,王树义的小儿子给他打来电话,哽咽着说:“俺李大爷,去世啦!”
那一刻,已是白发苍苍的王树义举着电话,呆愣良久,泪流满面。
事实上,后来很多个瞬间,王树义也都会想起在七里寺的那个夜晚,想起三个人头对着头,眼睛里闪着亮光,一起畅谈未来的那个场景。
李清泉来之前,李书记做简单介绍。此人的经历可谓跌宕起伏,相当精彩。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十五岁就扛起枪,跟着民兵,上前线打鬼子。在一次战斗中落单,自己一个人钻进玉米地里往回跑。十八岁被调到区里,按他的话说,自己大字不识一箩筐,干的却是扫盲工作。接下来,相继担任博城县某区团委委员、某镇团委书记,等等,后来调任淄城县,任某乡党总支书记,成为掌舵二十多个山村五千多口人的一把手。那一年,人家才二十七岁!因为性格耿直,说话不拐弯儿,在区委会上直接提问题,批评不正之风,遭到排挤,官降一级,任了乡总支副书记。人民公社成立后,改任公社宣传委员。直到一九六零年,当选淄城区管庄公社社长。
“刚好,他这两天回老家来办点事儿。你俩认识一下,山不转水转啊,你俩一个县的,说不定,哪天他就到你们公社去当领导了呢?”
这不,李书记这句话,转眼竟变为现实。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