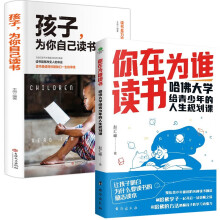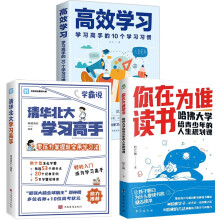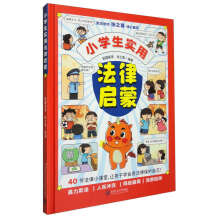红花不见了
深秋已过,十月的第一天已经到来了。清晨,薄薄的雾霭刚从田野里翻身,想要摇摇晃晃地离开地面,大别山脚下的一座农家小院里,就响起了一串清脆的声音:“红花,红花……妈,红花也不见了……”
“大早上的,叫什么叫?”一个老汉从屋里走出来,白胡子翘得老高。
“爷爷,您起床了?”一个圆脸的女孩笑着走过来。她十一二岁的年纪,个子不高也不矮,身材不瘦也不胖,扎着两根短短的辫子,脸上挂着两个浅浅的小酒窝:“爷爷,我还想给您做个鸡蛋汤补补身子呢,可是红花不见了……”
“霜叶啊,爷爷这身子骨,吃什么也没用喽!”老汉到底不再恼怒,翘着的白胡子垂了下去,声音也柔和了很多。
“怎么没用?您病了,就得吃点好的。”霜叶并不同意。她一边说着,一边在院子里又转了一圈。然后钻进了柴房,扒开了柴垛子。
这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朝南有三间不大的正房,中间是堂屋,两旁是睡房。小院的东侧,是矮矮的灶房和柴房。小院的西侧,有两间木棚子,一间堆着各种农具:锄头啊,镰刀啊,簸箕啊,箩筐啊,扁担啊……另一间则堆满了各种竹子:有整根整根的大青竹,有细细密密的竹枝子,有各种长短的砍得整整齐齐的竹节,还有一些劈得又长又薄的篾条。
此时,太阳刚从云层里露出点软绵绵的霞光,灶房的屋顶上就已经升腾起一股粗粗的白烟——不用说,早饭已经在灶上了。在灶上忙活着的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她穿着一件洗得看不出颜色的大褂,腰间系着一件旧衣服当围裙,正在把锅里做好的粗粮饭往外盛。只见她又往大锅里添了半瓢水,然后把夹着红薯丝的粗粮饭和着昨晚剩下的野菜,捏成一个个花花绿绿的浅褐色饭团,放在大碗里,粗瓷碗里顿时仿佛长出了几朵大蘑菇。等锅里的水开了,磕进去一个鸡蛋,加点盐,点点儿香油,撒把葱花,一碗鸡蛋汤就做好了。
闻着香味,霜叶也来到了灶房。
“妈,怎么还有鸡蛋?”霜叶扒着灶台问。
“等你起床再捡鸡蛋,小鸡都要孵出来了!”妈妈敲了敲她的头,把饭团和鸡蛋汤递到她手里,说:“端桌上去,吃饭了。”
天气还不太凉,早饭就在院子里吃。一张木头桌子,四把竹椅子,三个掺了红薯丝的粗粮饭团,一碟咸菜,两碗热水,一碗汤,三个人坐下了。霜叶把鸡蛋汤放到爷爷跟前,说:“爷爷,快吃,我一会儿就去把红花找回来!顺便也找找芦花和大花。花儿们都回家了,咱们就又有鸡蛋吃了!”
“嗯,去吧,棉花地里也可以去看看。”爷爷说完,把鸡蛋汤放到了霜叶跟前,又不放心地叮嘱:“小心当兵的。”
“爷爷,我吃完了,先走了啊!”霜叶抓起一个饭团,顺手拎起个竹篮,就跑出了院门。
“你看看,这哪里有个女娃样?女娃不像女娃,男娃不是男娃。”爷爷瞪了霜叶妈妈一眼,放下了筷子。“是,是,是我不对,谁叫我只生了一个闺女呢!”
霜叶妈妈说着,也拿起一个饭团,转身就回灶房去了。桌子上只剩下爷爷一个人,就着饭团,叹着气,慢慢喝着鸡蛋汤。
躲在门口的霜叶,也悄悄地叹了一口气。妈妈只生了她一个闺女,这件事情,一直是爷爷心中的一根刺。这根刺都扎在那里十多年了,却一直拔不出来。爷爷难受,妈妈难受,她也难受。可是,爷爷想要个孙子,继承他十里八乡巧手篾匠的本事,这个没有错。妈妈身子一直不好,快熬到三十岁,才拼了命把她生下来,妈妈也没有错。
P2-7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