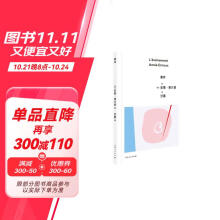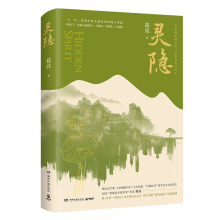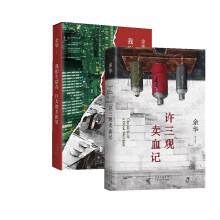在遥远的藏北高原一个名叫雪拉山的地方,有一片冰雪覆盖的墓地,其中一块墓碑上赫然写着我的名字。
两年前的今天,我离开了西藏。那天晚上,我彻夜未眠。子夜过后,我便悄悄拉开窗帘,静静地等待天亮。我想最后一次看着高原的天空一点点变亮。就要离开高原到零海拔的地方去工作了,但我的心里没有欢娱,只有悲伤。一种难以言表的悲伤在血液里激荡,仿佛随时都会冲破胸腔,淹没难忘的过往。真的不舍啊!高原毕竟留下了我三十多年的岁月,还有那些曾经与我朝夕相处、如今静静躺在冰天雪地里的战友。我这一走,何时才能重回高原,抚摸那些冰冻的墓碑,给长眠的战友点支香烟,洒一杯青稞酒?好在我的墓碑就在他们的墓旁,也算是另一种陪伴吧。我眼睁睁地看着窗外一点点变白。当高原的第一缕曙光刺破天空的那一刻。我禁不住热泪盈眶……今天傍晚,“拉动”结束回到营区,我发现手机上有两个未接来电。我给他们回过去。一个是早已预知的喜讯,另一个是始料未及的噩耗。在我还没来得及品味喜悦的时候,悲伤已汹涌而至。
半个月前,我来到长海县中队蹲点。长海县隶属大连市,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是东北地区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地方。这是我从高原部队调任辽沈总队两年来,第六次下部队蹲点。这次蹲点的任务是,指导中队战备演练。刚才,在中队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我突然下达了“拉动”命令,部队全员出动,仅用17分钟就成功处置了“情况”。这是一个标兵中队,军事素质很过硬。
部队演练结束,我独自离开营区,来到几十米之外的海边,坐在一块温热的礁石上,回复那两个未接电话。我先打给战友A,一连拨了三次才拨通。A的声音很大,一口四川话:“你晓得我在哪儿吗?”“你还能在哪儿,西藏呗。”“我告诉你,我在樟木口岸!”我心里激动了一下。那地方我很熟悉。八十年代末,部队从黑昌线撤下来后,我调到了中尼公路战线,在樟木边境待过两年。那地方有一段“之”字形公路,是著名的“三百米死亡线”,我的好几位战友牺牲在那里,掩埋在樟木云遮雾罩的烈士陵园里。
“哦,你小子跑到抗震救援一线去了?”“啥子小子?老子都五十多喽。”是啊,时间过得真快,我们都五十多了。他转业时没有回四川老家,留在了西藏,随后他把妻子和孩子也接到了拉萨。他在西藏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工作,妻子在拉萨一所中学当老师,是一位有点名气的女诗人。在雪拉山时,A就经常接到她两地书式的情诗。
A激动地说:“我们老部队正在这里抢险呢,你知道吗?”“央视新闻上天天有,全国人民都知道,我能不知道?”一个多月前,尼泊尔发生强烈地震,西藏日喀则聂拉木县和吉隆县的国道216、318线地段严重损毁,武警交通部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紧急抢险。后来又应尼泊尔国邀请,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救援大队500名官兵进入尼泊尔境内,抢修被毁坏的境外公路。18天后,尼泊尔又一次发生强烈地震,救援大队冒着生命危险连续奋战20个昼夜,终于完成了境外抢险任务。
“救援大队凯旋了,我们在这里迎接呢!”“好啊,那你好好慰问慰问老战友!”“你猜我遇见谁了?”“谁呀?”“让他跟你说两句!”手机里响起一个声音:“你现在好享福啊,待在零海拔的地方醉氧了吧?你可别把我们这些西藏的老战友给忘了。”一听沙哑低沉的声音,我就知道是C。
“你这个总队政委也亲自上阵了啊?”“我们交通指挥部的司令员和政委两个将军都亲临一线指挥呢,我这个小政委还敢不上来?你要是还在西藏,你也得上!”电话那头又换成了A的声音:“你俩别瞎扯了,我还有正经事没说呢!我还遇到了一个人。你猜是谁?”我说:“你净说废话,那么多的老战友,我哪能猜得过来?”“告诉你吧,我遇见我儿子了。”A哈哈大笑起来,“这小子都一米八了,这回可给老子长脸了,不信,你问老c。”C说:“他儿子在我手下当排长,比他老子强多了……”正说着,电话突然中断了。我知道他们很忙,便发了一个“祝贺老部队凯旋!你们忙吧,闲时再聊”的短信。
然后,我给B拨电话。B原来是川藏线养护支队的支队长,三年前退出现役,他没有要求安置工作,而是选择了自主择业,现在西安一家私企当保安经理,月薪四千,加上国家每月给他的高原退役工资,生活还过得去。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内心的苦闷,他原来号令上千人马,现在手下只有30多个保安,一定很不适应。半个月前,他打电话对我说,他从西藏回来三年了,还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有些格格不入,感觉工作很无聊,内心很孤独。他说他准备辞掉保安经理,重新返回西藏去,在川藏线上的藏族小学去义务支教。一个退役上校,重回西藏去义务支教,让我这个老高原很是感动。但我担心他的身体是否还能适应高原生活。他说如果能适应,就在那里多待几年,适应不了再回内地来。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