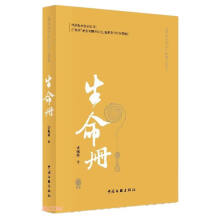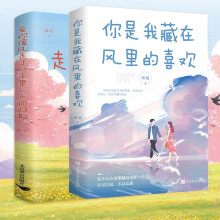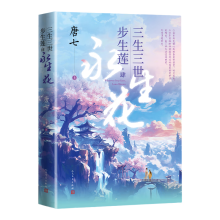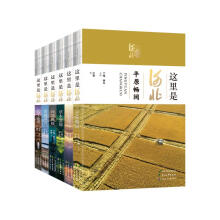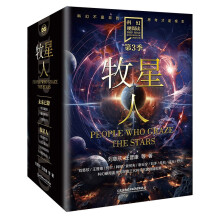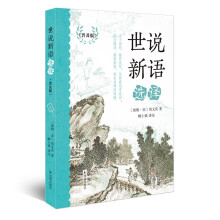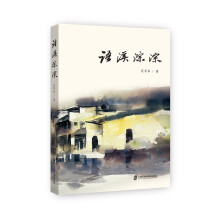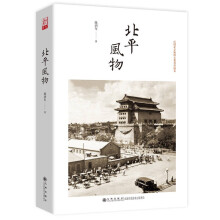《长河逐日》:
看着采访父亲的笔录,我发现,那些年并不如同他感受的那么舒适和安宁。十岁那年的遭遇,对那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就是灭顶的灾难。
“我十岁时,母亲得了大病,要死了,送去殡仪馆的慈善机构,那个机构是华人办的,当地无家可归的人、病重的人全去那里。我一个人伺候母亲,喂饭、买药、熬药。我母亲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之后,我们就住到伯父家里去了。”
一个十岁小孩,全凭一己之力,把病得躺在殡仪馆的收容所里等死的母亲抢救回来。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奇迹,也是一个《悲惨世界》主人公式的凄惨遭遇。那么,其他的人都哪里去了呢?他母亲之前不是在四姨太家帮佣吗?父亲没有说过他母亲发病前的情形,合理的想象是,何清突发急病,病势凶猛,东家眼见她救不过来了,就把她送去殡仪馆收容所,让她在那里度过最后时光。只有那个十岁小男孩不放弃,他不能没有妈妈,他也不相信妈妈就这样死去,他不离不弃,奋战不休。
回首这段难以置信的往事,父亲心平气和,没有一丝世态炎凉的感叹和孤立无助的悲戚,隐约间,反而流露着做成一件大事的自得。
何清虽然起死回生,但是他们母子之后的日子貌似更加不堪。
何清痊愈后,母子俩没再回到四姨太家,而是离开了他们一直居住的怡保,迁移去了几百公里外的海滨城市槟城。父亲没有说过这一变迁的缘由,我也没有问过。
奶奶何清在槟城还是给有钱人家帮佣,十岁的父亲则对这个更大的港口城市充满了快乐的好奇,他眼里的新环境是这样的:
“到了槟城,我母亲当佣人。母亲有一个朋友,是女的,在海边旅游地看厕所,那里有自来水,可以冲洗。进门一毛钱,给手纸,地很干净,都可以睡觉。”
父亲带着夸耀的口吻,明显地对新环境很满意。可以想象那时的场景:一个保姆的孩子,跟着母亲去拜访在当地居留的朋友,她们的社交场所,就是朋友工作的公用厕所,这个小孩没有觉得妈妈跟朋友在厕所见面聊天有什么不妥,因为这个厕所是他从未见过的洁净所在,远远超出了他经验中厕所的层级,以至于他觉得都能躺在厕所地上,再进一步推想,在这个收费厕所里,因为他们是管理人的朋友,很可能他和母亲上厕所都免费了。这让他对新环境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认同和自豪。
父亲的满意,也不全是小地方的穷孩子到了大城市后的眼花缭乱,还因为他进了更好的学校。
“我就读槟城的时中小学,地名叫爱情巷。我读了五、六两个年级,成绩很好。在我读过的学校,老师都非常器重我。”
成为他喜爱的新环境中的一员,这是一个孩子最高的快乐了。
2017年2月25日,我在马来半岛的骄阳下,找到了爱情巷,也找到了巷子里的时中小学。乳白色的两层西式建筑校舍,紧挨着巷子的一边,在阳光下明亮得耀眼。校门上“1929”四个阿拉伯数字,俯视着巷子里熙熙攘攘的游客。
爱情巷,是槟城的一个名片级别的旅游点,这所小学有八十八年历史,至今还是正规学校,为这条巷子平添了历史的积淀,也增加了旅游的价值。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