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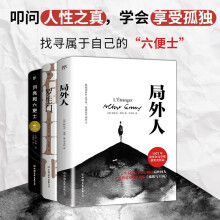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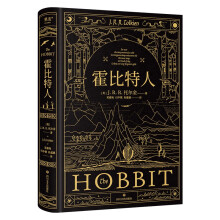




我常常和小提琴手泰瑟在一起,他很喜欢我,怀着志同道合的喜悦夸赞我的作品,预言我将会很有成就,而且随时都愿意和我一起演奏音乐,但是我仍旧觉得缺少了些什么。我挂念着莫德,却继续回避他,我没再听到珞蒂的消息了。我为何感到不满足呢?我责骂自己有忠诚且杰出的泰瑟为伴还不知足,但是我感觉泰瑟身上也缺少了些什么。我觉得他太过开朗,太过阳光,太过知足,仿佛不知低潮为何物。他不喜欢莫德,有时莫德在剧院里演唱时,他会看看我,悄声说道:“你看,他又在敷衍了事了!这家伙完全被宠坏了!他不演唱莫扎特的曲子,他自己知道原因。”我口头上必须承认他是对的,但实际上却不是真心这么想,我仍旧依恋莫德,可是并不想为他辩护。莫德有着泰瑟没有、同时也不了解的特质,而将我们牵系在一起的就是这些东西,那是无穷的向往,渴望与不满足。它们驱使我去学习与工作,激励我去接触人群,正如莫德也是一样,他被相同的不满足感以另一种方式折磨着、纠缠着。我知道自己会继续做音乐,但是我也怀着渴望,希望之后的创作也能够出于幸福、富裕与永恒的喜乐,而非总是起因于渴求与内心的匮乏。啊!为何我无法透过自己所拥有之物,透过我的音乐变得幸福呢?而莫德又为何无法透过他所拥有之物,透过他野性的生命力以及他的女人们变得幸福呢?
泰瑟是个幸福的人,他未因无法达成的渴求而受到折磨,温柔无私地喜爱着艺术,除了艺术所给予的,别无所求;若撇开艺术,他则更是个知足之人,因为他只需要有几个好友相伴,偶尔喝杯上好的葡萄酒,空闲时到郊外走走——这是因为他喜欢健行和呼吸新鲜空气——这样就够了。若按照神智学的教义,这个人具有最接近完人的条件,他的本性是那么的良善,极少让激情与不满足的情绪进入心中。即便如此,我希望——如果要我告诉自己的话——我不想变成他。我不想变成其他人,虽然常常觉得抑郁,但我想做我自己。自从我的作品慢慢地有了回响之后,我开始感觉到自己拥有力量,而且觉得自豪。我必须找到通往人群的某座桥梁,我必须通过某种方式与他们共存,而不是一直当个弱者。如果现在没有其他途径,或许我的音乐能够引领我走向人群;就算他们不喜欢我,他们也必定会喜欢我的作品。
诸如此类愚蠢的想法挥之不去,但是只要有人肯要我,只要有人真的理解我的话,我已经准备好奉献自己、牺牲自己。难道音乐不是这世界的神秘法则吗?难道地球和群星不是和谐地循序运转吗?难道我就应该孤零零的,一定找不到性格可以与我契合共鸣的人吗?
我在异乡度过了一个年头,刚开始的时候,除了莫德、泰瑟和我们的乐团团长罗斯勒之外,我很少和人往来,但是最近我的社交圈变大了,我对这个圈子并没有特别的好恶。我的室内乐作品演出之后,便和剧院以外,城里的其他音乐家熟识起来,现在的我承受着一种轻松愉快的负担,这是由于我的声名在小圈子里逐渐增长,我注意到人们知道我是谁,他们在观察着我。在所有的名望当中,最甜美的阶段,是尚未飞黄腾达,尚无法引起妒忌,尚未被孤立起来的那种名望;享有这种名望的人在外走动时,会感受到自己四处都受人瞩目、被人提及与夸赞,会遇到友善的面孔,看到认同的人赞许地点头,年轻一辈敬重地问好,而且还会一直存有一种秘密的期待,就像所有年轻人一样,认为最美好的事物即将到来,直到他们发现最美好的事物已然出现过了为止。对我的愉悦伤害最大的,始终是在肯定我的人身上感觉到那些许同情,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他们是在怜悯我,他们之所以会那么友善,全是因为我是个可怜虫,是个瘸子,而人们乐于给予我一些安慰。
在一场表演了我的小提琴二重奏的音乐会之后,我结识了富有的制造商老板尹姆多,他是位热爱音乐的朋友,乐于赞助优秀的青年音乐家。他相当矮小而且安静,一头逐渐灰白的头发,看起来既不像个有钱人,也不像有艺术涵养的样子,但是从他对我所说的话,可以知道他非常了解音乐:他不会一天到晚不停称赞,反而是给予冷静而中肯的赞美,这种赞美更有价值。他告诉我他有时会在家里举办音乐晚会,有古典乐,也有新式乐曲。这件事我早已从其他渠道得知了。他邀请我参加,最后并说道:“我们也演唱您的歌曲,我们都很喜欢您的作品,如果您能来的话,我的女儿也会很高兴的。”
在我尚未去拜访之前,就先收到了一封邀请函,尹姆多先生询问是否可以在他家表演我的降E大调三重奏,他已安排好一位小提琴手和一位大提琴手,两人都是才华洋溢的业余爱好者,假使我有兴趣一起演奏的话,将会保留第一小提琴手的位置给我。我知道在尹姆多公馆演出的职业音乐家都能获得优渥的报酬。我不是很想接受这场邀约,但是我并不清楚这封邀请函是什么意思。最后我还是接受了邀请,那两位合作的演奏者来我的住处拿取乐谱,我们排练了好几次。在这期间,我前往尹姆多公馆拜访,但是没有碰到其他人。就这样,预定演出的夜晚来临了。
第一章 序
曲第二章 初 恋
第三章 口 角
第四章 邂 逅
第五章 幻 灭
第六章 母 亲
第七章 喝 彩
第八章 夜 谈
第九章 追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