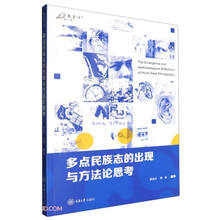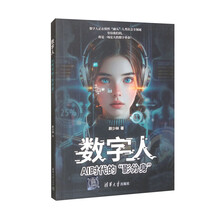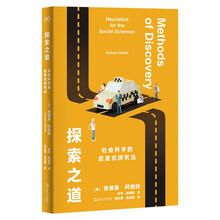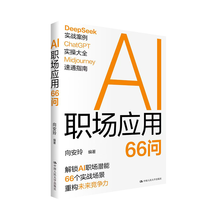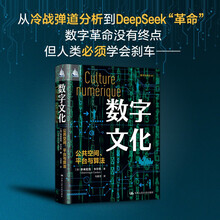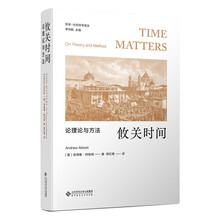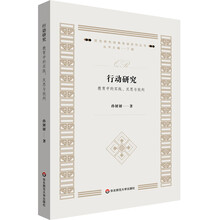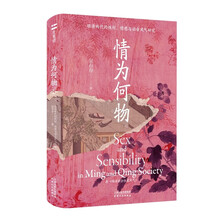法律的力量来自理性,但是这样一种力量是如何具体发挥作用的呢?这就涉及到法律中的理性是如何“实现自身”的问题,而这种实现的方式,简言之就是“程序”。人们希望每一件纠纷都能得到公正的解决,但是怎样在不同的情况下都能保持这种公正呢?这就需要有一个普遍的、大家都认可的、公正的操作方法或制度来帮助每一项公正都能获得落实。这种制度和方法便是“程序”。
程序本身其实也是体现着理性的光芒的。举个例子,为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联合国制定了一系列的协商机制和表决机制,这些程序都是有力地维护世界和平的制度保障。但是2003年3月14日,美国绕过了联合国的表决程序,一意孤行动用武力攻打伊拉克,这其实是一种破坏程序公正的行径。因为假如通过正常的联合国表决程序,美国无法在投票中获得多数票赞同,就不能通过“程序公正”这一关,所以为了达到目的,美国只能绕开程序。这从另一方面正说明了“程序公正”可以避免不正义行为的产生,所以我国政府强烈呼吁解决伊拉克问题要在联合国的框架内进行,就是出于依靠程序公正来维护世界和平的考虑。理性的程序本身就是实现理性的目的的有力保障。
那么怎样的程序才称得上是理性的呢?这主要可以从如下三方面来理解。
首先是程序的普遍性。法律的本质在于调节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把失衡的、不公正的关系纠正过来。所以,这就要求法律程 序必须是向所有的人开放,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通过诉诸于这个形式来求得公正,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由于经济原因而一时无法得到法律援助的人,可以要求暂时不交纳诉讼程序的费用或干脆就申请免交,因为经济拮据不能构成取消程序普遍性的原因;另一方面,由程序产生的结果对于所有人也同样是适用的,而且是具有强制性的。法院的执行庭就是专门负责判决结果的执行事宜的。那种“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封建特权在法治社会一定要被取消,否则无从体现普遍性。
其次,程序必须是独立的。原告与被告都要执行同一套程序,所以为了维护程序的公正性,原、被告双方都无法通过操纵和改变程序,或者是影响程序的执行人——法官来使自己从中获益,所谓程序的“绝缘性”指的就是这点。程序只有独立,才能赢得信任,才能获得权威,才能充当仲裁者和调节人的角色。但有人要问,程序可能是独立的,但执行程序的法官不一定是没有偏见、秉公执法的。确实,人总有自己的利益,绝对公正的也许只有神,但也不能因噎废食,一方面既然能成为法官,那么其个人素质还是已经被认可了的;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设计另一种程序来制约法官,比如复审制度、上诉制度;虽然程序由人制定,但是一旦制定了,它就要凌驾于所有人之上,包括制定它的人。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是由总统任命、经国会批准的,但是,最高法院的判决对于行政和立法两大机构都具有权威。
第三,程序的执行必须有时间性。换句话说,程序必须是在一定时间内有限的,官司不可以无休止地打下去,有开始就要有结束。过分漫长的诉讼过程,会使作恶者侥幸免于惩罚,使申诉者对程序失去信心,因此,程序的执行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结束,并产生出结果。
以上三点是一套公正的程序必备的条件。它们共同的特点在于三者都是形式性的,正是形式性的才是程序公正的充分必要条件,因为形式性杜绝了人为因素的掺入,这乃是西方法律传统的精髓,也是我们实施“法治”,结束以往那种由领导说了算的“人治”的关键之一。
“砸它,还是告它”
2001年的12月26日,在湖北武汉的街头出现了离奇的一幕:水牛拉着豪华奔驰牌轿车游街,随后5条大汉抡起木棒和大锤当众狂砸奔驰车。当问及砸车的理由,车主表示无法忍受奔驰公司糟糕的售后服务。砸车事件后,全国上下对不满意商品“一砸了之”的事件屡有发生。面对这样一些事件,多数消费者也许会觉得砸车长了消费者的志气,给那些仗着店大欺客的商家当头一棒。但是痛快归痛快,买得起奔驰车的老板可以一时性起砸车,一般的工薪阶层买了什么伪劣产品,恐怕这么处理的不会是多数。毕竟砸车是一个损己不利人、两败俱伤的下策。
其实砸车引出的是一个消费者理性的问题:消费者怎样理性地保护自身利益?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有个必要的前提,就是它必须是一个法制的社会,法律以其公平和公正性充当着市场经济中买卖双方的仲裁者的角色。国家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权益特意颁布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各地方也成立了消费者协会,用组织的力量来替被侵权的消费者讨回公道,每年的“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也会有各种法律咨询活动;各省、市、自治区都开通了“12315”消费者权益保护热线。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