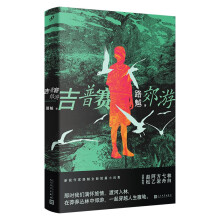第一章
1992年。广州郊外。维摩诘公墓。
昨夜,通宵的雷雨。这在南方的秋天是常有的事。在黎母山的时候,雷雨要比这座城市的雷雨来得恐怖,自然也更令人欣喜。那样意味着可以歇息,不必穿上汗臭烘烘的工作服,到晦气沉沉的原始森林里伐木。麦灿辉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公墓里静悄悄,坟堆上有几只乌鸦在聒噪。这么早就哭丧!麦灿辉自觉有些晦气,嘟囔着披衣起身。
屋子里进了水,地上满是泥泞,墙脚长出几朵鲜艳的毒蘑菇,很骄傲地舒展着。口有些渴,像火在烧。他不记得肖邦、方炜、林大头他们什么时候走的。反正不到午夜,他已醉得人事不省。半夜里惊醒过一回,见到一个女吊,很快又睡死去了。雷雨在什么时候停止的?他一点也不知道。
刑场离公墓不远,一片人迹罕至的山坡。那里似乎很热闹。说是九点钟行刑,可还没有到七点,那边已聚集了好些看热闹的人。麦灿辉心头一阵收紧。不管如何,到了这个时刻,眼看着一个熟悉的人,在自己眼皮底下被活活地枪毙,都是一件难受的事。
他看过《羊城晚报》,他也就仅读这一份报纸。报纸近来常在报道一个叫陈新宇的女人,贪污了几十万巨款,供自己的未婚夫挥霍,自己分文未花,但法律无情,锒铛入狱了。麦灿辉对此并不十分在意。一个陌生女人犯事了,与自己有什么相干?自己已经活得够腻味了,谁来关心自己?
昨晚,肖邦他们突然光临这间神憎鬼厌的守灵人小屋,给他带来一个消息:明早九时,将在附近的刑场枪毙昔日同在海南黎母山农场的农友陈新宇。
陈新宇?麦灿辉努力回忆这个名字及与这个名字有关的女人模样。
那时他只知她叫陈萍,一个鞋厂工人的女儿,模样长得有些怪,到处平平的,像只板鸭。人们并不怎么在意她。她也很少言语,见了人却常常莫名其妙地脸红,低眉顺眼的。他实在没留下什么印象。
肖邦他们用车拉来许多酒,都很低度。他知道自己这些农友很体恤他,既反对他酗酒又常常给自己送酒。没法子,谁让彼此都在黎母山里同过好几回生死呢!
关于陈新宇的案子,大家都没什么话说,彼此都在尽量避开这个话题。只是相约,明早多通知几位农友,到刑场去为她送终,让她看上一眼也好。
他们都知道,陈新宇只有一个多年鳏居的父亲,他终日酒瓶不离口,除了上班混几个工友喝酒外,便蹲在电线杆下与人杀车马炮,赌几个酒钱。父女几乎形同路人。知青们谁也没有上过她家。她实际上自回城之后便被人淡忘了。
雷雨已经停了许久了,空气里弥漫着重重的草腥气。墓地里一片静谧,乌鸦还在那儿不停地噪着,如丧考妣。麦灿辉突然踏着泥泞,冲上一个坟堆,捡起一块压着纸钱的土坷垃,向那群乌鸦掷去。
土坷垃没有击中鸦群,却砸在一座十字架上,那是一个香港基督徒的墓碑。墓碑很湿,土坷垃的粉屑粘在那十字架的交叉处,像一团血。
麦灿辉感到一种不祥。
他狠狠地拧开酒瓶子,猛地喝了一大口。酒气直冲肺腑,他打了一个寒颤,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刑场那边已很热闹,也许死因是个女的,所以附近的农民和放暑假的学生,早早地便来了。
他的眼光落在十字架旁边的曼陀罗上。
他们喝得醉醺醺地离开麦灿辉的小屋,沿着公墓的通道,东摇西晃地走上公路。林大头的那辆二手“平治”在细雨中闪着蓝光。车轮下积着许多雨水。他们钻进“平治”,雨突然大起来,炸雷滚过墓地,在黑黝黝的树林里炸出一片闪电。惊心动魄的火光瞬间熄灭在黑暗中。淌着雨水的车窗玻璃上映出三张冷漠而有些痉挛的脸。
林大头发动了汽车,揿响了镭射音响,是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
肖邦昏昏欲睡,头歪在方炜肩上。
“平治”颤动一下,轿车在雨中的公路上冲锋着。车厢里一片酒气。林大头打着嗝,难受地捂着胃部,他的胃病随着酒精的进入即时发作。三人中唯有方炜算是清醒。他心脏不好,不敢豪饮。
车灯照出一片朦胧的前路,汽车开始歪歪斜斜地像个醉汉,在公路上肆无忌惮地奔驰着。方炜见状不好,用手猛推林大头,让他把车停下来,林大头满不在乎:“喝一斤半斤算什么?喝得烂醉照样把车开到100迈。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