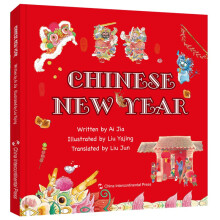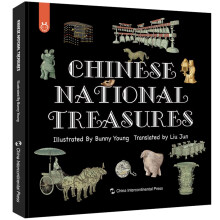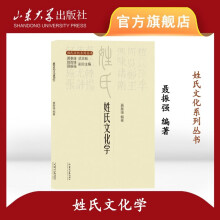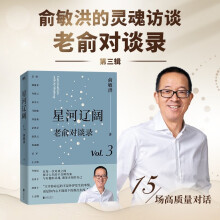《生生不息》:
历史上,不同地域、不同生存背景的族群,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形态。文明总是在不断冲突中浴火而生,淬炼成型,经过长时间的积淀,沉入到每一个文化共同体成员心灵深处,成为其文化符码和心理结构,这样就构成了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根据,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一个民族的进步,离不开对各种文明的吸纳和交流。孤立的文化系统是一个缺乏生命力的静态系统;断绝与其他各种文明类型进行信息交流的民族是一个缺少生机与活力的民族。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在各种文明类型的冲突与融合中走向浑厚壮大的。
中国文化是融合了多种文明类型的文化。这一特点,不仅表现在中华文化绵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即便是从其源头来看,也能够看得出来。就地域来说,有黄河流域文明,有长江流域文明,有草原游牧文明,有森林渔猎文明等,而每一种文明形态都有其鲜明的文明气质;就思想类型来看,有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思想文化。到汉代以后,从印度传人了佛家文化,并很快本土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不管是不同地域的文明,还是不同类型的思想,它们并不是孤立存在、单向发展的,而是一直处在不断交融、互补的过程中,相互制约,彼此促进,从而形成了一种多元共生、百花齐放,同时又具有内在和谐关系的圆融结构。
实际上,任何一种文明类型,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正是在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互补共进。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与吸收各种文明类型,从而形成骨肉丰盈的文化形态。例如,中原农耕文明具有文雅从容、趋于内向的特点,草原游牧文明具有粗犷简约、趋于外向的特点。经过不断地融合,农耕文明吸取游牧文明的长处,游牧文明也接纳农耕文明的成果,经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等多层面的交流沟通,最终趋向融合统一。本章中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新诗和到是明年》等故事所揭示的不同文明形态的交流,并不仅仅停留在器物服饰、文学艺术层面,在更深层面上,隐含着游牧文明、渔猎文明和农耕文明在冲突融合过程中的对彼此文化成果的认同和接纳。
思想文化也是这样。儒家崇尚人世有为,道家主张遁世无为,法家主张霸世力为。以《诗经》为代表的黄河文明温柔敦厚,以《楚辞》为代表的长江文明浪漫瑰奇。在最初的历史时期内,两者各成一脉,独立发展,各具特色。随着南北文化大规模的交流与融合,以及百家思想的争鸣交锋,在各种历史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各种思想文化、各种地域文明不断融合,共同发展,形成了中华思想文化特质鲜明而又丰富多元的面貌。例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将各方文化杂糅而成为新儒家,南北文化在交融里,诞生了新的机体;魏晋南北朝时期,外来的佛教和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逐渐渗透进中国文化的根里,儒家将佛教和道教的宗教理论与哲学思想选择性地加以扬弃,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的宋明理学,儒家文化在创新和改造里获得了新的生机。近现代,中国又放眼世界,向西方积极学习政治、科学、技术等文明成果,融入了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本章编选《儒道互补》《汉家自有制度》《法显求法》《鸠摩罗什译经》《容闳之志》,意图就在于传达中华文化这一融合的过程。
回顾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我们会发现,历史上中华各民族之间既有兄友弟恭、和平安乐的和谐局面,又有刀戈相向、征战不断的混乱局面。但是有一点不能否认,那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各兄弟民族共同组成的文化共同体。虽然历史上有分离乃至反目的时候,但是各民族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是在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发展与演变的几千年历史中自然形成并客观存在的。只不过由于受历史的局限,在没有外部对立物的情况之下,这种一致性经常不能成为各民族的自觉认识,各民族间的隔阂掩盖了相互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呈现了中华各兄弟民族在冲突中实现融合的努力。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