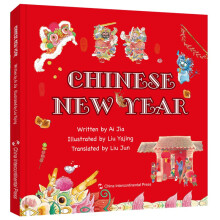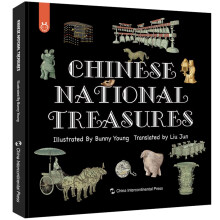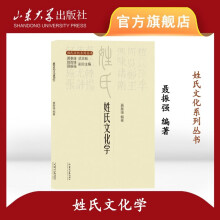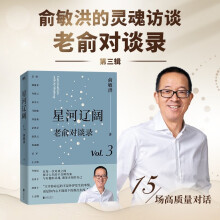《家国情怀》:
东汉的严植之,有着极为清高的个人操守。自己辅佐的人获罪,别人都怕受牵连,避之唯恐不及,只有他挺身而出帮助发丧。路上遇人病人膏肓,别人都怕被误解惹麻烦,只有他连病人姓名都不问,就将人带回家中去救治。严植之的所作所为需要极大的勇气。萧子良是南朝最著名的慈善家。他曾因笃信佛教而招致一些人的非议,但在助人济困方面,他恰恰将佛教徒的慈悲襟怀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谁有了困难,都可以来找他;百姓受灾,他便拿出自己的钱,大力施救;有人贫病无告,他就在自己家后面加盖一排房子,免费收留并医治他们。这些善行,一部分是出于他的责任,更多的则是源于扶危济困的信仰。辛公义看到当地百姓因害怕疾病传染而放弃患病的亲人,就把病人都接到自己办公的地方,日夜和病人待在一起,从而证明疾病并没有传染性。然后再责百姓以孝悌之义,最终使得当地民风日益淳朴。此类善行不断涌现,表明古代的贤士大夫从来都是把行善当成人生准则的,所谓“兼济天下”,除做官要尽做官的责任,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以外,还要利用一切可能在百姓身处困境时造福百姓。
为了更好地劝善,封建社会里,人们常常宣扬“善有善报”“福泽子孙”这样的宿命论思想。比如《齐东野语·朱氏阴德》中就记载,朱承逸救人、帮别人偿还债务的那一年,朱家刚好添丁增户有了朱服,朱服日后官至中书舍人,而其他子孙也有所成就,让朱氏一门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此类因果报应的说法在民间流传甚广。对此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待,阴德也好,因果报应也好,当然是种迷信思想,不值得相信,但是善言善行确实能够改变人的气质,影响人的思想,进而成为影响家庭教育的重要因素,有祖辈言传身教,子孙后代出现几个小有成就的名人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修身济民是知识分子的自觉行为,积德求福是民间行善的强大助力。在这两种思想的影响下,读书人乐于行善,民间百姓也同样认可善行,社会也就逐渐形成了一种以行善为荣、以助人为乐的良好之风。特别是每当盛世,天下太平而无战乱之时,民间就会出现大量的善人善举。范蠡作为古代商人的杰出代表,善于致富,更善于“散财”,堪称古代富商扶危济困的第一人。隋朝的李士谦和唐朝的宋清也都是这样的富人。特别是药商宋清经营药材助人不求回报的故事,生动地诠释了追求商业利益与承担社会责任两者可以兼顾。宋清高价收购良药,平价卖出,看似利润微薄,可是当他占领了市场,赢得了口碑之后,医生就成了他忠实的伙伴,患者就成了他最佳的宣传渠道,他的生意自然也就越做越大。对病人来说,买药是来救命的,付得起药费的人可以得到好药,治好了病自然会感激他;付不起药费的人在他这里也能通过赊欠得到好药,自然更加感激他。在他眼里,善心是第一位的,而这恰恰也是医药行业的社会责任所在。从这点上来看,宋清的所作所为对当代社会来说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与上述这些人相比,郑板桥的善行则兼具传统与现代的特征。一方面,他的行善还是基于宗族的亲疏关系。在考中进士后,他嘱咐弟弟,把薪俸尽散给家族里的穷亲戚和过去的老朋友;向最重要的人表示关心之后,如果还有剩余,再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另一方面,他对于施惠者与受惠者在人格上的平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说,自己与没考中进士的老朋友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自己比较幸运。谈到佃农时,他又说“彼称我为主人,我称彼为客户,主客原是对待之义,我何贵而彼何贱乎?”从这两处都可以看得出,在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心中,已经开始有了人格平等的意识。他的善行绝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而是充满了对受惠者的尊重。互相尊重与人格平等这一点,正是现代慈善的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的行善传统除民间的个人行为之外,还有着鲜明的自上而下的特征。从西周到晚清,中央政府在从事慈善事业上一直没有缺位。每当大灾来临,从京城到地方,各级政府都会开仓放粮,赈济灾民,还有些地方政府成立了一种平抑米价的机构,米价贱时收米,米价贵时平价卖出。历朝历代也都有鼓励各级地方政府和民间大户施粥的传统。汉代“文景之治”时期如此,到北魏孝文帝时期更是如此。宋代是慈善事业发展的高峰,从朝廷到民间,都出现了大量慈善机构。崇宁五年(1106),北宋中央政府诏令在全国推行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南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政府又命“天下诸州建慈幼局”。在士绅中间则义庄,最典型的当属范仲淹在苏州创建的“范氏义庄”。范仲淹早年生活艰苦,和改嫁的母亲相依为命。或许跟幼年时的这一段经历有关,他在晚年创立了义庄,庇护贫穷的范氏族人,避免其流离失所、迁徙他乡。范氏义庄的规矩详尽,从钱物的发放,到对仓房、田地的管理,对管理者的监督等,都有具体详尽的规定。这一义举也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范氏后人一直严守祖训,使得义庄前后延续八百多年。范氏义庄可谓开启了古代慈善的一个新时代,很快就成为各地官绅争相效仿的对象。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