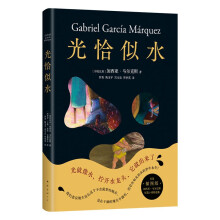千万别和魔鬼赌你的脑袋
——一个含有道德寓意的故事
(1841)
拉斯托雷斯的唐?托马斯在其《爱情诗集》之序言中声称:“Con tal que las costumbres de un autor, sean puras y castas,imporó muy poco que no sean igualmente severas sus obras.”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说,这意思就是假若一名作家自身道德高尚,那何为他作品的道德寓意就无关紧要了。我们可以假定唐?托马斯因下此断言而进了炼狱。而且为了诗的公道,一个明智的做法就是让他待在那儿,直到他的《爱情诗集》售罄绝版,或等到他那些诗集因无人问津而被束之高阁。每一篇故事都应该有一种道德寓意;而且说得更贴切一点儿,批评家们已经发现每个故事都有这种寓意。菲利普?梅兰希顿三百年前曾写过一篇关于《蛙鼠之战》的评论,证明了荷马的宗旨是要唤起一种对骚乱的厌恶。皮埃尔?拉塞纳则更进一步,他证明荷马的意图是要劝说年轻人节食节饮。正是这样,雅各布斯?胡戈也已经彻底弄清,荷马是以欧厄尼斯暗讽约翰?加尔文,以安提诺俄斯影射马丁?路德,以食忘忧果的民族挖苦全体新教徒,以哈耳庇厄揶揄所有德国人。我们更现代的训诂学者也同样深刻。这些先生证明《洪水之前》中有一种隐藏的意义,《波瓦坦》中有一则道德寓言,《知更鸟》中有一种新的观点,而《小拇指》中则有超验论。一言以蔽之,只要一个人坐下来写作就不可能没有一个深刻的立意。一般说来,这样作家们倒省了不少麻烦。譬如说,一名小说家用不着去担心他的寓意。它就在那儿,也就是说它就在什么地方,寓意和批评家们能自己照料自己。时机一到,那位小说家想说的一切和不想说的一切都会在《日晷》或《新英格兰人》等杂志上曝光,另外还会加上他本来应该想说的一切,以及他显然是想说而没有说的一切,结果寓意那东西到最后全都会老老实实地出来。
因此,那些不学无术的家伙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对我横加指责,说什么我从未写过一篇道德小说,或说得精确一点儿,是从未写过一个含有道德寓意的故事。他们并不是上帝派来使我扬名并启发我道德感的批评家——那是秘密。不久之后《北美无聊季刊》就会使他们为自己的愚蠢而感到羞耻。与此同时,为了阻止对我的伤害,为了减轻对我的非难,我献出下面这个悲伤的故事。这个故事的道德寓意无论如何也毋庸置疑,因为任何人只消瞥一眼就能从这个故事的副标题中看到寓意。我应该因这样谋篇布局而受到赞扬,这样谋篇远比拉封丹之流的故事结构更为明智,因为拉封丹之流总是把效果保留到最后一刻,到故事结尾才让读者看到其寓意。
“别让死者受到伤害”是古罗马十二铜表法戒律之一,而“替死者讳”是一项极好的禁令,即使被提到的死者是微不足道的小民。所以,我的意图并非是要诽谤我死去的朋友托比?达米特。他曾是个无赖,这一点儿不假,而且非常悲惨而可耻地死去,但他不应该为他不道德的恶习受到责备。那些恶习之养成是因为他母亲身上的一个缺陷。当他还是个婴儿之时,他母亲就尽其全力用鞭子对他进行教育,因为履行义务对她那井井有条的头脑来说总是件乐事,而婴儿就像咬不动的牛排,或像现代希腊的橄榄树,当然是打得越多越好。但是,可怜的女人!她不幸是个左撇子,而用左手去打孩子那还不如不打。地球的旋转是从右向左。打孩子万不可从左向右。如果说从正确的方向一鞭子可以抽掉一种不良倾向,那可以推测,从相反的方向一鞭子会抽进同等量的邪恶。托比受惩戒时我常常在场,甚至从他蹬腿踢脚的方式,我就能看出他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坏。最后我终于两眼噙着泪花看到,那条恶棍已完全无可救药。有一天他挨耳光一直挨到满脸发黑,黑得别人会以为他是个非洲孩子,可结果除了他扭动着身子昏了过去,那顿耳光没产生任何效果,我不能容忍再这样下去,只好立刻跪倒在地上,提高嗓门儿预言了他的毁灭。
事实是他恶性的早熟令人不寒而栗。他五个月大时就常常大发脾气,以至于不可能咬清楚字眼儿;六个月大时我曾亲眼看见他咬坏一副扑克牌;七个月大时他就养成了抓扯和亲吻小女孩儿的习惯;八个月大时他就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在戒酒誓约上签字。就这样一个月接着一个月,他在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到他满一岁的时候,他不仅坚持要蓄胡须,而且染上了赌咒发誓的恶习,并用打赌的方式固执己见。
正是由于最后这个卑鄙下作的习惯,我所预言的毁灭最后终于降临到托比?达米特头上。那个习惯“随他成长而成长,随他健壮而健壮”,所以待他长大成人之后,他几乎是不打一个赌就说不出一句话。这并不是他真正下注打赌,绝不是。我得替我的朋友说句公道话,他要真正下注,保管彻底输光。对他来说打赌仅仅是一句套话,仅此而已。他在这一点上的言辞表达没有丝毫的意义。那些话很简单,如果并非全是虚词,一些用来完成句子的富有想象力的措辞。当他说“我和你赌什么什么”,从来没人想到接受他的打赌,但我仍然禁不住认为制止他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一个不道德的习惯,我这样告诉他。这是一个鄙俗的习惯,我请求他相信这点。社会一致反对赌博,在这点上我说的全是实话。国会明令禁止赌博,在这点上我绝对无意撒谎。我规劝告诫,但无济于事。我举例论证,但徒费口舌。我苦苦哀求,他一笑置之。我动情央告,他哈哈大笑。我晓之以理,他冷嘲热讽。我威胁恫吓,他诅咒发誓。我踢他,他叫警察。我扯他的鼻子,他趁机擤一擤,并与魔鬼赌他的脑袋,说我再也不敢劝他改邪归正。
贫穷是达米特的母亲特有的生理缺陷留给她儿子的另一种恶习。他穷得叮当响,而毫无疑问,这正是他打赌时闪烁其词而很少真正下注的原因。我不敢说我曾听到过他使用“我跟你赌一美元”这样的措辞。他通常使用的措辞是“我跟你赌你想赌的”,或是“我跟你赌你敢赌的”,或是“我跟你赌句废话”,要不然就还是那句更有实际意义的“我跟魔鬼赌我的脑袋”。
这最后一种赌注似乎最中他的意,这也许是因为他承担的风险最小,因为达米特已经变得非常吝啬。万一有人接受他打的赌,他的脑袋本来就小,因而他的损失也就不大。不过这些仅仅是我的个人想法,而我不敢肯定我这样想他是否正确。总之,那句话越来越成为他的口头禅,虽然把脑袋当作钞票来打赌极其不妥,但这一点是我朋友倔强的脾性不允许他去理解的。到后来他完全抛弃了其他形式的打赌,决心只说“我跟魔鬼赌我的脑袋”。他这种专一的顽强性和排他性使我感到的不快不亚于给我造成的惊奇。凡是我说不清原因的事都总使我感到不快。难以理解的事总逼着人去思考,而思考则有损健康。事实上,达米特先生在说出他那句无礼之言时脸上总有某种东西,他发音吐字方式中的某种东西。这在一开始还显得有趣,但后来却令我感到非常不安。由于眼下尚无确切的术语为这种东西命名,请务必允许我把它称为费解,不过柯尔律治先生会把它称为玄妙,康德先生会把它称为泛神,卡莱尔先生会称它为歪曲,而爱默生先生则会称它为超验。我开始完全讨厌那种东西。达米特先生的灵魂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我决定要发挥我雄辩的口才去拯救它。我起誓要像爱尔兰编年史所记载的圣帕特里克为一只癞蛤蟆尽力那样为他尽力,这就是说“要让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我立即着手履行这项义务。我再一次对他进行苦口婆心的劝告,竭尽全力进行最后一次直言诤谏。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