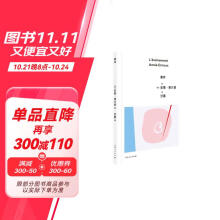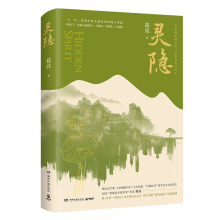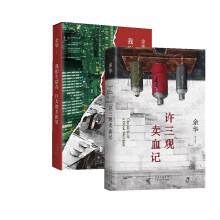《曲水流觞》:
我最后一次站在校门口搜寻那条希望的土路的时候,天色几乎暗下来了。那个时候幕阜山里没有电灯,人们为了省点煤油,天不黑尽是没有人点灯的,如果换成现在,恐怕早都万家灯火了。
半下午时喝的两小碗菜粥早已化作尿排掉了,我敌不过夜的静寂漫长和心中的馋念,在母亲的呵斥下洗了手脚准备上床,这个时候父亲回来了。父亲被两个农民架着,一瘸一瘸地出现在门口,父亲头上脸上糊满了血污,衣衫褴褛,那副箩筐被别人挑着,满满一担金樱子。
两个农民把父亲轻轻地安放在竹椅上,对我母亲说,杜校长在葫芦尖上摘金樱子摔了跤。
那个时候父亲早就摘去了校长帽子,只是一个打钟的勤杂工,那些农民还尊称他为校长。父亲很高兴,大声对母亲说,快把坛子搬出来,倒酒给这几个朋友喝!
母亲一边让座,一边满脸难色地抱怨父亲说,酒早都叫你喝光了,哪里还有酒?
这一下轮到父亲脸红了。父亲就是这样,碰到高兴的事,碰到投机的人,他就大声嚷着请人喝酒,他忘了家中早就没有了酒,他忘了袋里早就没有了钱。
那几个农民也不给父亲难堪,连连说着客气的话,一边退出门去了。
母亲打了水来,帮父亲擦洗满身的血污。母亲找出一把松明,准备去请个跌打郎中帮父亲治伤。父亲制止道,一点破皮伤,哪需要请郎中。金樱子一点都没损失,皮肉受点儿苦,值得,值得。父亲两手扎满了金樱子的刺,有的已深入皮肉,一动,便龇牙咧嘴。
我不解父亲付出头破血流的代价采来一担金樱子有何用处,这东西当得饭吃吗?
我小时候有遗尿的毛病,夜里睡得死,隔三岔五就要在母亲辛辛苦苦洗干净的被子上画上一幅不规则的地图。母亲气极时就用竹梢子抽我的屁股,父亲拦住她说,你这方法不灵,你看我怎样治他。晚上吃饭的时候,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半瓶酒,他咕噜噜地仰着脖子灌了一喉咙,看了看,还剩一二分深浅,恋恋不舍又浅浅地抿了一口,然后对我说,儿子,张开嘴——父亲趁我张开嘴的一瞬,将瓶中的那点残酒全倒进了我的喉咙。我大声咳嗽,脸红耳赤,肚子里燃起了一团火。一连几个晚上,我没有遗尿,父亲就炫耀地对母亲说,怎么样?
其实,真正治好我遗尿毛病的并不是酒。有一回,父亲从山上采回来一捧熟透了的金樱子,铺在地上,用鞋底除去满身的毛刺,然后一个个剥开,去掉里面坚硬的籽粒,就着一个猪小肚,用文火熬了半天。我吃了那罐汤之后,从此就断了遗尿的根。
过了几天,父亲把那担金樱子挑到供销社,换回一坛供销社酒厂酿制的薯丝酒。
换酒的那天晚上父亲没有回家,母亲猜想父亲在外头喝多了酒,就在别人家睡了。那个时候,没有电话,更没有BP机、手机、小灵通之类的通信工具,而且,母亲也知道父亲是个命大的人,那么惨烈的车祸都毫发无损,出门与朋友喝几盅酒更不会有什么不测。
天亮之后,母亲起床,到厕所里倒马桶。走出房间,朦胧中看见路中间躺着一个人。母亲知道那是露宿的乞丐,便没好气地埋怨,屋檐下祠堂里哪里不好歇,偏偏要拦在路中间。走近了,忽然间闻到一股酒气,再一细看,却是我的父亲醉卧路中。父亲旁边,倒着一只黄狗,那狗吃了父亲呕吐的酒菜,也醉倒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