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飞那么低,”一个男孩兴奋地说,“我看见了飞行员!”
主人和奥凯奥马首先走出去,走到了公路上。奥凯奥马只穿了汗衫和长裤,看上去瘦小了很多。奥兰娜依旧抱着宝贝坐在地上,结婚礼服上裹着迷彩衬衫。乌古站起来,朝公路下方走去。他听见恩瓦拉医生对奥兰娜说:“让我来扶你。灰尘会弄脏你的裙子。”
一条街以外的玉米研磨加工点附近,一个院子冒着浓烟。两栋房子倒塌了,满地都是灰尘和碎石,一些人发狂地在乱糟糟的水泥堆中挖掘,嘴里说着:“你听见那哭声了吗?听见了吗?”他们的身上蒙着一层薄薄的银色尘土,看上去像是眼睛睁开、没有四肢的鬼怪。
“孩子还活着,我听见哭声了,我听见了。”有人说。男人们、女人们都围拢过来,帮忙,瞪大眼睛仔细看;一些人也在碎石中挖掘,另一些人旁观,还有一些人尖叫着,打着响指。一辆车正在燃烧;一个女子的尸体倒在边上,衣服全被烧光了,烧黑的皮肤上到处都是粉红的斑斑点点,有人用一个撕坏的黄麻袋盖住了这具尸体,但乌古仍能看见那双僵硬的、漆黑如木炭的腿。天空乌云密布。即将到来的降雨带来了一股潮湿的味道,与烟火燃烧的气味混杂在一起。奥凯奥马和主人一起在碎石堆中挖掘。“我听见了孩子的声音,”又有人说,“我听见了孩子的声音。”
乌古转身离开。地上有一只样式时髦的凉鞋,乌古捡起凉鞋,看了看真皮的绑带和厚实的楔形鞋跟,又放回原处。他想象着穿这只鞋的时尚的年轻女子,为了跑到安全的地方,甩掉了这只鞋。他想知道另一只鞋在哪里。
主人回家后,乌古坐在起居室的地板上,背靠着墙。奥兰娜正在拨弄着碟子里的一块蛋糕。她仍旧穿着结婚礼服;奥凯奥马的军装衬衫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椅子上。客人们都慢慢地离开了,他们几乎没说话,面容暗淡,布满歉疚,仿佛是他们允许空袭破坏了婚礼,因而异常不安。
主人给自己倒了一杯棕榈酒。“你听到那条新闻了吗?”
“没有。”奥兰娜回答。
“我们的军队在中西部占领的地盘全丢了,向拉各斯进军的行动也完蛋了。尼日利亚现在说这是战争,不再是一场警察行动。”他摇摇头。“我们被出卖了。”
“你想吃蛋糕吗?”奥兰娜问。蛋糕摆在中央的桌子上,除了她切掉的那一小块,基本完整。
“现在不吃。”主人喝下棕榈酒,又倒了一杯。“我们要修一个地堡,防止再次发生空袭。”他的语气正常、冷静,仿佛空袭是仁慈的行径,仿佛刚才近在咫尺的不是死亡。他转身对乌古说:“你知道什么是地堡吗,我的好伙计?”
“知道,先生,”乌古回答,“就像希特勒的那个。”“嗯,对,我想差不多。”
“但是,先生,有人说地堡是集体坟墓,”乌古说。
“绝对的胡说八道。地堡比趴在木薯地里安全。”
屋外,黑夜已经来临,偶尔一次闪电,照亮了天空。奥兰娜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尖叫:“宝贝在哪里?宝贝在哪里?”说完撒腿向卧室跑去。
“我的爱,”主人跟在她身后。
“你没听见吗?你没听见他们又来轰炸我们了?”
“是打雷。”主人从背后揽住奥兰娜,抱紧她。“只是打雷。被我们的雨师挡回去的雷雨终于自由了。只是打雷。”
主人抱着奥兰娜,持续了一会儿,奥兰娜终于坐下来,又给自己切了一块蛋糕。
4.书:《我们死去时世界沉默不语》
他辩称,尼日利亚在独立前没有经济。殖民政府实行专制,一种表面仁慈实则残忍、以惠泽英国为主旨的独裁统治。1960年的经济构成是潜能:原材料、人力资源、高昂的士气,以及英
国人拿去重建战后经济剩下的经销管理局的储备金的一部分。还有新近发现的石油。但尼日利亚的新任领导人过于乐观,在推行行将赢得人民信任的发展项目上过于雄心勃勃,在接受剥削性的国外贷款方面过于天真,在盲目模仿英国,又过分热衷于全盘接收尼日利亚人长期以来无从拥有的傲慢态度、更好的医院和更高的工资。他勾勒出这个新国家面临的复杂问题,但重点讲述1966年的大屠杀。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对“伊博族政变”的报复,抗议行将导致北部人在政府文职机构中失利的《中央集权法令》——并不重要。死亡人数的不同统计数字——三千、一万、五万——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屠杀令伊博族感到恐惧,加强了他们的团结。重要的是,大屠杀使得之前的尼日利亚人变成了热忱的比亚法拉人。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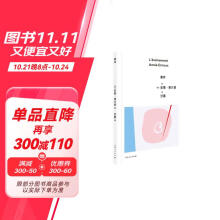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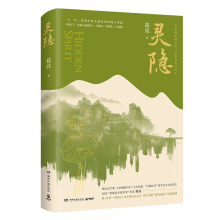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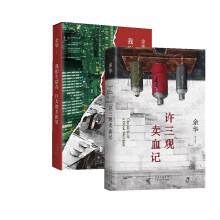







——《纽约时报》
《半轮黄日》是一本惊人的杰作,有着充沛的智慧和对人物深刻细腻的刻画——这本书是继阿契贝的《瓦解》和V.S.奈保尔的《大河湾》之后,又一部极具分量的20世纪的经典之作。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我们一般不用“智慧”这样的词语形容新人,但这位年轻的作家具有古老的讲故事的人身上的那种智慧……阿迪契拥有天纵之才。
——钦努阿·阿契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