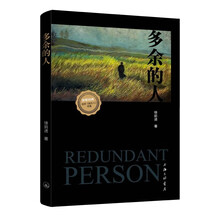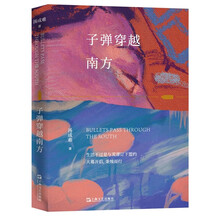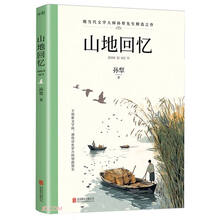说出来你可能不信,27岁时我当过一段时间记者,遇见过一些人,听过不少离奇的故事,但始终不如在A城经历的那个故事强劲。我对它印象至深,因为我至今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故事总有两个版本。
那是我刚从Y城辞职后,抱着休整一段时间的心,接了一个老同学在A城揽下的活。这活说起来不难,记录一个文化酒店项目的全过程,我的工作类似于做纪实文学——说普通点,就是当个“场记”——留下项目人物的丰功伟绩,以便日后歌颂。在去之前我把曾经写过的一些故事和报告文学发给他们,老同学说可以,够用,我便去了。
A城并不繁华,相比我待过的Y城,地方小,发展节奏慢,我去的时候正是深秋,梧桐树上的叶子正要掉光。一排排树,配以两边沉如墓室的灰黑色高楼,秋风中再飘下几片枯叶——整个城市到了冬天就像从坟里挖出来的,令人压抑得说不出话来。
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天气、这样的景,造就了A城一批文人。他们长年累月地在萧瑟中感怀人生,杰出的人物拿了茅盾文学奖、见诸报端;不知名的文学爱好者们像孑孓一样游离。他们常常三三两两相聚,或在酒吧,或在茶室,夜深人静时酌一壶酒,能聊一宿风月之事。
我去的那个项目里自然有这样的人,负责的老板就是。他姓陈,年逾四十,虽然是个商人,但偏爱文艺,所以做了这个和中式文化有关的酒店项目。他保养得很好,爱运动,也爱内修,所以看起来像是三十五六,血气方刚“正当年”。和他吃过几次饭后,你就能知道他为人爽直:爱酒,爱上等白酒,喝起来那叫一个大方,茅台随随便便能干掉一斤。
他身边有个秘书,姓杨,叫杨曦妤。她是一个单亲妈妈,和我一样从Y城来到A城。她看起来眉目清秀,温文尔雅,常着中式古典服装,好似古时候的大家闺秀。因此遇到她的人都不厌她,我对她也颇有好感。小杨平常打点办公室事务,工作不算太忙,但也相当紧凑。平日我也和她对接,凡是需要我到场记录的事件,都由她负责通知我,知会我材料和注意事项;有时她叫上我一起陪同领导会客,重要的客人如银行行长、政府官员,我都得备份记录下。这件事的必要性在于,白天大家的正经会面往往聊不出什么,到了晚上自由之风总能扑面而来,吹散陌生人之间的拘泥和紧张。因此那些出人意料的话语、惊人听闻的故事,也往往从夜宴里传来。对我这样的记录者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
有一次,陈总请了A城的一个作家、一个杂志主编、一个年轻摄影师,还有几个政府官员一起吃饭,叫上了小杨和我。陈总说,“晓萍你以后可是文化人,多学点东西总是好的”,我便去了。这顿饭不同往常,饭局设在A城郊区偏僻的山间,驱车需20公里,一行人到晚七点才摸到一个坐落在路边村子里的小栋别墅。看起来那就是村民自家的宅基地,小门小院,进去后却别有洞天。
主持这间屋子的人姓端,也是这家“馆子”的大厨。大家都叫他“老端”,显然他与文化界名流相熟,墙上的字画、厅堂里的摆设,虽然简单,但能嗅到名贵的味道。陈总和一行人进门后就开了话匣子般谈起了字画,指着堂间的镇店之宝,说这是某陈姓书法家的大作。既是他本家,又喜欢收藏字画,可求了老端小半年,他都不肯卖,陈总也只有来吃饭才能赏味。宾客们听了陈总的话齐齐打趣,“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一一走近那幅镇店之宝,用手机拍下字底下的落款。陈总大笑说:“老端做的菜也是极好,来来来,到里面坐。”
里面的包间又不同于厅堂。玄关的木几上只摆了一座瓷器,瓷器呈奶白色,透亮饱满;内里插着一支刚开苞骨朵的花枝,散开微微清香。宾客们自然敏感,纷纷意识到这必也是大家之作,陈总笑着介绍说,这花瓶出自A城某隐居江西景德镇的陶瓷艺术家“大姚”之手。大姚一日来老端家吃饭,吃得兴起,就赠他一个花瓶。“也是无价之宝啊!”陈总两眼熠熠地感慨道。
兴许是特别的艺术氛围催生了特别的自由——不同往日大谈金钱之事,这顿饭一开局,陈总就问作家:“哎,你那画家朋友,现在还和电视台那主持人在一起吗?”
我默默一惊,看作家——气定神闲地嚼着水煮花生,不吱声,只笑;身旁四十多岁的女编辑嚼了一口凉拌马兰头,大声应道:“早分了!你不知道啊!和他艺术学院的学生搞一块咯!”
“哈!哈!哈!哈!”陈总大笑四声,笑声如京剧里唱念做打的腔调,既带着蔑视,又充满同情,仿佛千帆阅尽的过来人似的,摇摇头说:“啧啧啧,老牛被嫩草绊了噢!”
桌上其他人都在默笑,女编辑显然和他更熟一些,“你还担心人家老陈,人家是牛吃草,你是草吃牛,都要把你掏空咯!”
嚼着花生的作家不禁笑出了声,呛了一口花生末,连忙倒上茶水“咕噜”几下漱口。陈总面露难色,立马打岔道:“讲什么呢!喝酒喝酒!”众人立马举杯豪饮,身旁的小杨默不作声,脸涨得通红——我便一下明白了。
那晚大家都喝嗨了,聊了许多艺术圈的风流韵事。对我倒是轻松的一晚,因为实在没什么可记的,这顿饭算白白吃了一顿。到晚十一点,小杨见我打车回去太远,便留我去她家住。她有个保姆,平常带孩子一起睡,让我和她睡一床,我就答应了下来。
对公司里的桃色新闻,说实话我并不关心。毕竟A城的景与气候我都不喜欢,我想做完这个项目肯定走人。过去在Y城待了一阵,我也养成了一个不好的习惯,当每个人都像空气。现在小杨于我,也没有特殊到哪里去。不过她倒是热心的人,一回家立马为我翻出一套玫红色睡衣,帮我调好洗澡热水,又忙不迭地打开客厅和卧室的两个空调,烘足马力到三十度。在我踏进她家后十来分钟,这个位于A城中心一个中档小区里130平方米的大房子,瞬间每个角落都变成了春天。
我洗好澡后,穿上小杨的玫红色睡袍,有点不适应。她睡衣上有股特别香艳的气味,像Y城高档百货里常能闻到的味道,但我不记得是哪种——我看着洗手间梳妆台上的瓶瓶罐罐,全是名牌,还有的根本叫不出名字……我偷偷打开一罐,往自己身上喷了喷。
小杨见我洗完澡,问我要不要涂点润肤乳。她说女人的身体比脸还重要,倒让我联想了一些不好的事。
我说:“空调可以关了啊,这么大房子,太浪费了。”
“没事,尽管用,自己舒服才好。”她趿拉着拖鞋,去厨房里泡一壶玫瑰茶,细细糯糯的声音从厨房里传来。
泡好茶,小杨捏着两个精致的小骨瓷杯走来客厅。我坐在铺着白色羊毛垫的软皮沙发上,她站着把一杯清澈的玫瑰茶递给我,冷不丁说了一句:“其实人生没什么意思,最重要还是对自己好。”
我一下接不上话,只好接过她的茶,“唔……”。
“其实老陈对我挺好的。”
“嗯?你说陈总?”我没想到她会聊这个。
“是的。平常我只跟熟人称老陈。今天你也听到了,他们取笑我。不过我习惯了。”
小杨背过身去,打开桌上的香薰灯。
“你和陈总……”我尴尬地问。
“不是你想的那个关系。就是很好的朋友。他很照顾我。”
“噢……我也没多想。”
“能理解。女人嘛,本来就是弱势群体。更何况我是离了婚的女人,还带着个孩子。”
“你也挺不容易的。”我说。
“他们见不得我爬这么快。我一个女人家,初来乍到,还不是靠自己拼?”
“嗯,你一个人带着孩子,还要养保姆,是挺难的。”
“这房子月租七千,保姆一个月七千,我儿子周末还要上辅导班,一个学期一两万。这还不算我自己的开销……我知道他们怎么想,想我凭什么啊,还不是凭老陈。笑话!我就不能靠自己了吗?!”
“你压力一定很大吧。”我从未见过小杨如此强势的一面。
“我早就当孩子他爸死了。从我怀孕时我就当他死了,不指望他给我们什么钱。我从Y城到这里来,就是想重新开始出人头地。一切的一切,都为了我儿子!”
说到儿子,小杨的语气有点激动,她声音微微发颤,但强忍住了没说下去。
我说“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以后尽管说”,虽然我掂量着自己也帮不上什么,但还是说出了这句话。
“谢谢你晓萍,我们都加油吧。”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