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是一本坊间常见的杂文集子,就是把发表在报刊上的千字文拾掇拾掇,出本书。但是由于作者的身份不一样,这书就有了独特的魅力。妹尾河童是日本当代著名的舞台设计家,今年74岁,一直活跃于戏剧、歌剧、芭蕾舞、音乐剧、电视等表演艺术领域,曾获“伊纪国屋演剧”、“艺术祭优秀”等众多奖项。所以在写杂文之余,河童也不免手痒,以自己商标式的画风,即一种略显稚拙的工笔素描,为杂文里涉及的方方面面事物画插图。这些事物虽然细小,但在河童的文笔和画笔下,显出别样的情趣。比如意大利自动制面机、伊朗红茶、香港地铁车票、意德法各自的电话卡、东西方的钥匙和锁、印第安水车、印度纸币、马来西亚风筝、丹麦和巴基斯坦的捕鼠器、英国火柴、墨西哥面具、日本的桥,甚至……莫扎特的大便。三联同时还推出了妹尾河童的另一部作品《窥视印度》。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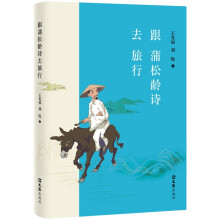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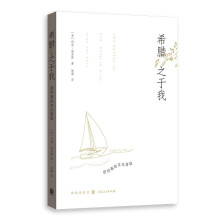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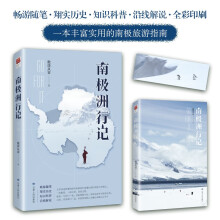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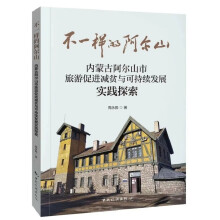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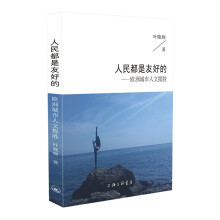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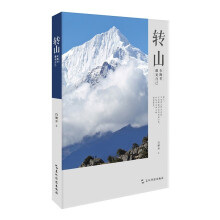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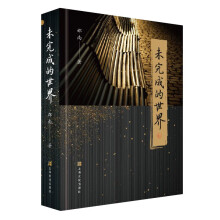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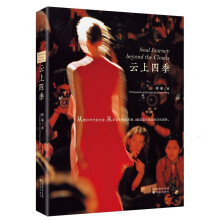
两年前我写了《印度在窥视里》,那是我头一回读到妹尾河童,读到了既极讶异,亦极兴奋。委实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有趣的老顽童,马上把他和黄永玉归为一类,甚至立即将他在心目中的地位归置到黄永玉之上,因
觉得他更为细腻也更为智慧,和黄的彪悍不是一个路子,性相近,习相远的缘故吧。如此写来的书评完全成了一篇百分百的颂歌,字里行间充满了赞誉,且来看看那篇也许言过其实,却也不无道理的颂歌——
妹尾河童是个男的,是个到过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男的,是个而今已经74岁了的日本男的,并且他还是一个很能够画几笔素描画,很能够写一些逗趣性质的活泼文章的日本男的。
这个1978年、1983年两度造访印度的日本老顽童从来不改好奇宝宝的本色,从来不顾众人的殷殷告诫,在印度“任意妄为”:喝生水、吃路边摊、净往高处爬,不怕拉肚子、脱水、感冒,拼了老命只为多看看印度的不同面貌。
两个年头,拢共一起不足三个月的时间里,这个老头在印度由南到北游历十八个城市与地区,搭乘火车、人力车、包租车,遍览辽阔的印度大陆所独有的宗教、建筑、文化、艺术、风土民情,奢华与赤贫同时并存的社会现象,都经由他用极力贴近庶民生活的观点与丰富的设计素养以及平实的文字和亲切可感的素描,向所有对于谜样的印度充满好奇的人们一一呈现。
一个地处南亚的文明古国,历数千年沧桑,辉煌都已成镜像,存留下来的因为得以存留都带着历史的痕迹,在岁月的长河中浴清了身体,亦淘汰了曾经的滞涩,显露出事物本身固有的光辉。
这样的光辉是最逗引人的,河童说:书中依旧照我一贯风格,把看到或者感受到的事物,用传达给亲朋好友的心情尽可能呈现出来——文字无法表达就画,图画无法呈现的就以文字表述。全部用手写也只是想让人有亲手奉上的感觉。
这样做出来的书,就如同一封一封信笺的集合,阅读的每个人都是收信的对象,信纸的那一头那个先到了异国的人向你娓娓言说那一个你向往中的国家,事无巨细,毫发毕现,让你喜悦着他的喜悦,惊奇着他的惊奇,也感动着他的感动。
过去的两年中,河童的书陆续由三联出版,出来了《窥视日本》、出来了《河童素描本》。我是每见必买,每买必读,一路追逐下来,直恨翻译太慢,干脆去学了一年日文。这样的礼遇实在超过了早年读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也超过了热血沸腾年代读村上春树。
妹尾河童究竟有怎样的魅力会弄得我追星族一般地成了“河粉”?到再见他如今这本最新的《河童杂记本》,我开始暂时消退一些偶像崇拜的情愫来理性地分析那魅力的根源。
想来想去,我想还是他的无由而来无由而去的随性生成了那股诱惑。河童真是个活得极自在的人,喜欢的东西太多,感兴趣的东西太多,永远如同小孩子一般对眼前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他在这新书后记中说:我喜欢吃幕间盒饭,也喜欢车站的盒饭,因为能品尝到各种各样的食物。
河童确乎就是这样来对待人生的,让他不去好奇,宁不如杀了他。让他一辈子只拥有一种眼光,大约他会疯狂。这一本书又是水藤节子催促出来的,她是一点不厌烦河童的“想起一出是一出”,就只想出一本“幕间盒饭”那样的书。各种各样的怪念头全罗列在一起,在别人一定是凌乱得不行,在河童倒是相得益彰,他骨子里就是那样一个“各种各样”的人的嘛!
他是窥视印度,花样百出;窥视日本,繁花似锦;行旅素描,千奇百怪。到了这本杂记,则更是将那“各种各样”表现到极致,写写画画,忽而谈访书,书倒不花篇幅去谈,却津津乐道地讲书的运送讲运书车车身上牢牢地冻着的冰雪,进而又去讲运输车车内书籍的堆放;忽而去谈“河童式”的海外旅行窍门,个中说到开罗的公车,原来抓吊车身的乘客比安坐车内的乘客还要多,因在开罗抓吊车身的一律免费,河童自然少不得要那样抓吊一回;忽而谈起他名字的由来,谈起老婆嫁来之日他的回忆,那回忆真是有趣:做我媳妇的人选倒有一个,风间小姐。可在她辞职后我们便断了信儿,再没有来往,即便向她提出,想必她也要说NO。弄到最后朋友看不下去,代劳求了婚。居然真就成就了一段美满婚姻!
我尤其喜欢看第三辑的杂学笔记,说尺寸、汉字、啤酒的泡沫:泡沫能吸附啤酒花的苦味,躲过泡沫饮用啤酒,能让舌尖免受涩味刺激,品尝到啤酒本身的柔和。让我们干杯。说水、咖喱、饭盒、钥匙和锁,从“钥匙和锁”的变化中感受到人类的智慧,让他百看不厌。还说地图、礼仪、磁石、远近透视图技法和工具,在比较中他认识到“比较,仅仅是了解彼此差异的手段之一”。
两年四册书,河童一如既往地杂记他多姿多彩的人生,这样的记叙和素描是永无餍足的,因篇篇是一扇窗,推开了,便能望见更绚烂的世界。在那里,印度和日本都是美丽的,随性的行旅也是,随意的杂记亦然。
读毕全书,阿川佐和子说“河童确实是怪人,不过他能把复杂的东西如此简单易懂、饶有兴味地描述出来,实在令人佩服。河童的幕间盒饭的味道实在令人意犹未尽。下次他究竟会做怎样的盒饭给我们,期待和震憾共存”。
两年前,妹尾河童74岁,而今,已是76岁的老人了。真希望他活得更长一些,用他那双上苍恩赐的眼睛引领我们去观望那属于他也属于众人的美好,给这苍茫的人世加添更多的色彩和乐趣。
文:三皮 《中华读书报》妹尾河童的旅行观
寂静山谷里一株昂首期盼的树,存在了许多年,只为等待欣赏它的人。而洞见生活细节的能力,原本就是少数人的专利。
三联书店推出了妹尾河童的两本书《窥视印度》、《河童旅行素描本》,看过的人一般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种是充满欣喜的惊叹:好有趣哇!另一种则是感觉完全不可理喻的:变态!因为有趣所以发现作者确实非同常人,因为“变态”,所以才有现今的有趣得已呈现书中,于是有趣与变态互相纠集,构成了河童文本的最初印象。
亲身体验式旅行 什么都要试试看
从来没见一个人这样旅行。什么都想试试看。在《窥视印度》中,他不顾亲朋警告,印度人吃的喝的,路边摊上的各种小吃零食,他都要尝试尝试,结果搞到连续几天腹泻不止,把卫生纸垫在裤子里继续上街“乱跑”也在所不惜。他从南到北造访了印度十八个城市与地区,印度的各种交通工具,人力车、三轮摩托车、公共汽车、火车等等,他也一定要乘坐一下。火车包厢里折叠起来的卧铺,打开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呢?躺上去什么感觉?也引得他苦苦思索,忍不住想要拆开来尝试一下。最有趣的是,他乘坐火车到达印度首都德里,看到火车站里很多人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于是这位河童老先生干脆放下手中的行李,也躺下去试试看。在他看来,只有通过各种各样的亲身体验,才是体会印度大陆所特有的生活人文的最直接和最令自己信服的方式。而这种身体力行在《河童旅行素描本》中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花朵到底能不能吃呢?不妨试试看,于是河童吃花朵吃到自己肚子痛。
我们不主张完全无知的尝试,但是我们不由得钦佩这种强烈的探知态度。记得儿童成长过程中有一个阶段,到手的任何东西都要放到嘴里尝尝,亲身体验,这何尝不是我们从孩童时代起认知世界的最本初的方式呢?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固守于已经获得的经验和知识而越来越疏离于这种认知世界最直接的手段了呢?一切都已司空见惯不再新鲜,一切都在掌握之中,真是这样吗?河童不但以他孩子般的探知心态,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他亲历的印度,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认知世界的“新”的旅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