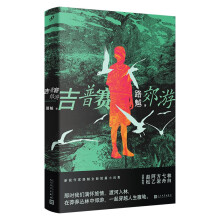第一章
1
长松岭这地方,寂寞了许多年。它残留的松柏,大都杈桠虬结、半边干枯、针叶萎缩作一堆,樵夫都提不起胃口。也有几株因地角倾圮,成为悬崖,远离了斧斤,细细瘦瘦,郁郁葱葱,指向天空。长年累月老鹰在断崖绿云育雏,黄花在顽石老藤自怜。白云经停,蓝天如盖。月枕风拂,冷径残碑。虽然非林非园,不山不丘,晓得历史的人来此逗留一会,便会觉得它气与天接,高与云平。
这天,刘莺和秀云走到这里来了。
姑娘小伙两天前相逢在一个旅游景区。秀云是台湾的育蝶人,当时,他对刘莺说一路上总有几只蝴蝶跟随你,别人都不奇怪,以为你头发上有什么香水,我晓得这和香水没关系。其中我还看见了稀罕的虎斑蝶、优酷粉蝶、红歌星蝶,恭喜你!刘莺姑娘只露个抿笑。
他俩后来便坐在一山麓小亭里说话。秀云说起一同来大陆的爷爷吴子宇,讥笑爷爷真是个无事忙,他这几年在海峡两岸穿梭来往,为过去的母校招魂。姑娘对此无甚兴趣,听着而已。
秀云又说爷爷可能是为母校招魂的事有眉目了,无事忙又有了新课题,要给他寻找爷爷。姑娘多少觉得新鲜,便问:“呃,这是怎么回事?”
“爷爷说我还另有一个亲生爷爷,很可能是当年抗日战争时的空军,名叫赵芸——不是常山赵子龙那个赵云,是草头的芸。”“嘻,抗日战争……空军……”“哈哈,遥远吧?”“也不算。那你的亲爷爷,他……”“牺牲了吧?其实关键是奶奶,战争中,奶奶下落不明,爸爸便成了孤儿,当时才两个月。我爸现在还在军队,所以提起往事,他总是一声不吭。呃,我爸叫吴鹰,我叫秀云,我奶奶叫杜芊。”
“嘻,连奶奶都介绍。”刘莺笑时轻轻眨动眼皮,这已令秀云中了几次魔,觉得她眼睛像对袖珍的荧光凤蝶,会翩翩飞动。
“因为奶奶才是关键。据说我的很多方面,如兴趣爱好这些,都是奶奶遗传。”“长得也像奶奶?”“唉,就是长得不像。奶奶别号叫七仙女,你可想而知!这不光说她的外貌——慢慢再给你讲。”
“慢慢再给我讲……”姑娘脸上挂着逗弄的笑容,“我呀,家有奥秘,我一定要去寻根究底,别个想还没有呢!还坐在这里闲扯……像时间不值钱!”“哈,你是说,我该丢下正事……”“正事不正事,正事做得再好,一个根都没有的人,吹过一阵风,天上一朵云,飘起的……”“哈,你说完!”“成不了大器。”“嗯,你不简单哪,说的话!”“简单不简单,就该听爷爷的!”“好,听你的!”秀云手一拍膝盖。“别乱说呀,我不够格当谁的爷爷!”姑娘眉尖儿蹙起,可话音落下后,又别过脸去“咯咯咯”笑起来。然后,像对自己骤雨般的笑感到不好意思,站起来要走。
秀云抢前两步:“我想约你……我们一起走!”这句话从他遇见姑娘,就在喉咙左冲右突,一旦撤去防守,顺口就出来了。
姑娘在听他说“恭喜你”,并看他一眼后,就在等这句话。可是,这人何人?她心里虽有七分喜,又还带三分忧。现在她有了主见:“哼,我晓得你想约的,是过去那个叫杜芊的女孩子。你把我当成了那个女孩子!”“鬼灵精,你能看透我的心!”“乱说!我呀,就是耍心重,想走遍所有好耍的地方。可是又怕累,歇歇走走,就像只蝴蝶。我从你说的,猜得到杜芊也像。”
两天后,姑娘便带秀云来到长松岭这个寂寞荒芜的地方。
没有路,他们只在野草乱石中走。忽然来一股风,于深草中吹出块碑状物。拨草一看,石上刻“空军坟”三个字。秀云十分惊讶,扭头看刘莺一眼。刘莺边揩着脸上汗珠,冲他一笑,还做个怪相。
他俩分头继续在荆棘草莽中搜寻。秀云找到两块碑石,可用指头一点点抠出字看,都没有“赵”字。忽听刘莺在叫他:“喂,你来看!”他遂奔过去。此前刘莺一点点在拖开一大堆荆棘,她如此执着,因为她从一个偶然的角度,看见在枝叶缝隙的深处像有块碑,怦然心动,她就锲而不舍将这些缠绕紧密绞结如蚕茧的藤蔓扯开,手指都刺破出血了,终于露出约有两尺高一段碑石,因为糊着青苔和泥土一个字也看不见。秀云跑过来将青苔泥土剥开,露出残字:上面一个字,左边剩一竖,右边一个寸,这大约是个“付”。字形太扁,还该有个字头。下面一个字,亦是上下结构,能辨识清楚的,上部右边是个“又”、下边是个“土”。他俩都难掩脸上的失望。
秀云站起对墓碑鞠躬说:“惊动了,真对不起!”蹲下将碑的四周收拾干净。抬头不见刘莺,便叫了一声。远远传来她的回答:“哦,就来——”秀云笑笑,原地站着。
刘莺来了,捧着件插花:一簇翠绿的松针上绽放着几朵玉兰、孔雀花干花,还有几朵这里的野花。中央伸出几条银白色的干枝,像火焰,像缎带,又像手指,飘飘袅袅指向天空。篮子是现用枝条编的。她将插花摆在碑前。
“咦,”秀云叫道,“真好看,又有韵律,你的手好巧哇!不过,这干花、干枝从哪里来的?包里随时带着的?”
“插花都有名字,”她笑道,“你取个名字。”
“天堂。”秀云不假思索道。
2
吴子宇偎着嘉陵江石门大桥的栏杆,享受江风的吹拂。江心那两只逆游的巨龟石还在。这两只巨龟石原是江上风景,江上奇观,如今它们恰好做成了大桥的桥墩。中国自古就有用活龟来垫柱脚的传统呢,这两块江心石状若巨龟,真应了它们的宿命。它们在江心快活自在了千万年,如今被人利用,这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总之人们再也看不见它们在江心自由冲浪的情景了。
这里旧名石门坎,“门”指的就是那两只巨龟石。也许正是这两只冲浪的巨龟石吸引了游慎敏校长,他才选中了这里,在这里建设东南工业专科学校的新家。
吴子宇还看得见两只巨龟在江心畅游。他眼中的沙滩洁白又柔软,同学们赤脚在沙滩上奔来奔去,踢球、晒太阳、游泳。还有人在沙滩上挖洞,把偷来的青香蕉埋进滚热的沙洞,但等他过两天再来香蕉就无影无踪了,好沮丧……他想着这些不禁笑了。过去这里有好多芭蕉园和香蕉园,他遂放眼望了学校那片芭蕉园,但那里现在已变成灰扑扑的建筑群。而河滩正在挖沙,满目疮痍。当年,校园被密密层层的芭蕉林包围着,那涌动的绿浪与白沙滩相映成趣,而且在视觉中与远处歌乐山上的松涛连成一片。
他不禁挠了挠自己变得光秃的头顶,觉得绿色稀少的校园故址就像人老了一样。
江上往来着张张白帆。那时汽船少见,往来的尽是白帆。运输当然是轮船好,但要说赏玩和观景,那还是要帆船才有诗情画意。上水船全靠赤膊的纤夫们,在他们的号子声中行驶。而同学们每日都和着纤夫的号子在读书,每日都被纤夫瘦削筋强的体型感动着。有的同学一遇机会还脱鞋下水、挽起纤绳,在这帮腰弯得像虾子的人群中添几只虾子,就差没打赤膊。
假日里,巨龟石总是托着一群青年学生,在冲浪,它背上的学生在忙着野炊。学生有的从江心取水,有的在钓鱼,有的在和船工喊话,说要买鱼。有时双方还隔着急流说些粗话和笑话——当然,要没有女生,另外还要方博士不在场。方博士和女生通常是同来同往的。方博士一般不会来嬉水,但是有女生去请他,说她们想玩又怕危险,那么他只要不是太忙,是一定会欣然前往的,这是他的绅士风度。
方博士是东工精神的重要推动者,对东工,除游校长外他最有影响力。方博士高高的个儿,方正的脸膛,白净面皮,讲一口标准的国语。学生们对他都敬畏三分,各种场合只要他威严的目光一扫,闹哄哄的人群立刻鸦雀无声。可他比学生又大不了多少,故在带领学生郊游时,他可以完全抛开师道尊严,就像个娃儿头。像此时吧,吴子宇偎在大桥栏杆上,还看得见方博士穿件短袖衬衣,长裤裤脚卷起,正和学生们在沙滩踢球,被沙子弄成了花脸;看见他离开前在江边洗脸之后还要用打湿了水的手指将头发梳理整齐……
噢,那里,鳞次栉比的楼房和工厂,曾是荒凉的而又苍翠的,静寂的而又火热的呀!片片的农田,片片的树林、香蕉林,还有片片的荒坡。石砌的东南工业专科学校校门质朴厚重。吴子宇籍贯少城,说来有趣,在抗日战争时期,东工迁渝的大队人马尚未到达时,这个高小才毕业的放牛娃就已在这处新校门走进走出了。若以对母校的感情排序,吴子宇一定排东工学生中的前列。而这一切——情感与经历——又源于他的小学老师温漱玉。他揣着一颗在农家孩子中算得上细腻的心,目睹了温老师与东工游校长的相识与相爱。
吴子宇上高小时,班主任温漱玉还是个少女。抗战开始,东南工业专科学校从南京溯江而上,在少城暂时扎下营盘,谁料得到,它在吴子宇心里就永久扎下了营盘。后来东工和温老师都走了,到重庆去了,吴子宇也偷偷跟到了重庆。他在重庆当报童,当小工。后来他又回少城读到初中毕业。
初中毕业在少城已经相当于秀才,可以在乡下教初小或进城谋一份像样的工作了。但他还一心一意要读东工。衰败的家景使一家人已经好久没有笑模样了,瘦骨嶙峋的父亲躺在竹凉椅上抽水烟。他对儿子说道:“儿啊,爹没有钱供你再念书了,你念书就念到这里了吧!”
可他对父亲道:“爹,如今家里的景况不好,两个妹妹又小,按理我该去找一份事情做,或者就回家种田吧,来挑起家庭的担子。可是,我如果读得更高一点,那对家庭对国家都更有益呀。至于念书的钱,也有不收费的学校。”
“啊,有不收费的学校?”“东工呀!东工是五年制专科,招初中生。而且是公费,不要家里一个钱。另外,还有师范也是公费。爹,我想去考东工!只是爹你的身体……”
他紧张地等着父亲的回答。他未料到的是,父亲不仅点头应允了,而且在他枯瘦的脸上浮起慈祥的、欣慰的笑容。因为父亲的这个笑容,所以在两年之后,以及在这五十年之后,当他跪在父亲的坟前时,他并不特别的难受和特别的后悔。在他读东工的头年里父亲就去世了,他未能尽孝和奔丧。
他千里奔波到重庆去报考了东工。出考场时他碰见了游校长,羞于自己在考生中显得很寒酸,且自我感觉题做得不好,便赶紧低下了头,要快步走过去。但游校长将他喊住了,说了几句话。之后,他为了保险还去考了一所师范学校,遂回家里苦等消息。
师范学校先于东工发榜,他名落孙山。众所周知,东工对成绩的要求高于师范,他已经灰心了。但仍有那么一线希望吧?所以东工没发榜他就不愿出去找事情做。
这天他在自家田里薅秧,因有几个初中同学来了,他从田里上来,带着两脚的泥水,就和同学在路边的大黄葛树下说话。天气闷热,没有一丝风,只有知了的叫声一片,吵得人直想捂住耳朵。他说起重庆的学校只有东工还未发榜,而英语和数学自认都只能得六十几分,根本无希望了呢。正在叹息之时,有位女学生模样的姑娘坐一乘滑竿到了,就在大黄葛树边停下滑竿歇气。她见这几个小男生垂头丧气的样儿,就细心听他们说话。因听见吴子宇在说考东工,她便笑着问:“你叫什么名字呀?哎,正巧,这是我刚离重庆时买的一张报纸,上面登了东工发榜的名单,你拿去看吧!”
她起身揭起了垫在石头上的报纸。吴子宇慢吞吞地走过去,一脸无所谓的神气,榜上无名的坏消息,倒不如不看。报纸在他手里有些抖,当他看见自己大名列在航空机械科的倒数第二名时,他竟哭了!这姑娘和那几个同学相顾讶然,想起范进中举的故事,怕他会疯。当他拭着泪跑回家时几个同学连那姑娘都跟在他后面。及至他在父亲面前破涕为笑时,及至他母亲笑眯眯地为大家煮荷包蛋吃时,大家才跟着笑了。
那姑娘爱笑,从少城嫁到别处,五十年后已满头银丝了。吴子宇还打听到了地址去看她,她说起当年吴子宇“中举”的情景,还一说一个笑。又追问他为何师范落榜却考上了东工?这问题吴子宇想了五十年却依旧答不上来。游校长治校严格不徇私情是出了名的,吴子宇不愿对任何人说出他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游校长在录取他时破了一次例。那么游校长为什么要对他破例?是游校长被他眷恋着东工的深情感动了,还是温老师给游校长写了信的?对此他至今没有问过温老师,而且他永远也不会问。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