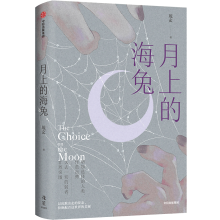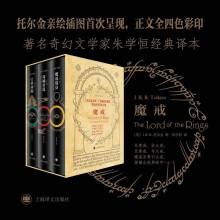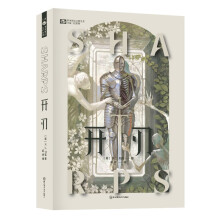我在黎明来临前静静走进室内,在黑暗中找到我仅有的象征阿瓦隆的信物——我从薇薇安遗体上取下来的小小的弯刀,它与我身为女祭司时随身佩带,在逃离阿瓦隆时又丢弃的那把刀一模一样。我悄悄将它系在腰间,系在我的外衣之下。这把刀永远不会再离开我,它将与我一起下葬。
我把它藏在身上,当作那晚唯一的纪念。我甚至没有给我额上的新月重新染色,一部分是因为尤里安(他一定会问起),一部分则是因为我知道我还不配拥有它。尤里安把自己手臂上褪色的蛇形刺青当成装饰,像是提醒他曾有过、后来放弃的身份;但我不会这样看待我的新月印记。接下来的几个月,甚至几年中,某部分的我就像玩偶,尽到他要求的所有职责——纺纱织布,调制草药,照料儿孙,听我丈夫讲话,帮他绣锦衣华服,在他生病时照顾他……这些事我都不多思考地去做,在他短暂而令人厌恶地占据我身体时,我的躯体便完全麻木,只用最浅的意识应付。
但当我再度学着计算从春分到夏至再到秋分的太阳潮汐时,不时摸摸那把小刀总带给我安慰……我像个孩子或见习女祭司一般,痛苦地以手指算着日期。还要好几年,我才能再度感到太阳潮汐在我的血液里流动,才能精确地知道太阳或月亮会在地平线的哪一点升起,能够再度像过去那样对日出月升致敬。同样,在夜晚,当周遭所有人都入睡后,我会仔细观察星曜,让它们旋转移动的力量在我的血液里流动,直到我成为静止土地上的轴心,头顶的星辰都环绕着我舞蹈,像季节轮回。我晚睡早起,以便有时间用找寻药草或树根当借口,走到山里寻找古老力量的痕迹——从竖立的石头到锤形池……这是令人疲惫的工作,我花了好几年才在尤里安的城堡附近找到几样。
但即使是在头一年,当我仍在与褪色的记忆搏斗,试图找回多年前所学的知识时,我也知道我并不是孤军奋站。始终有人守护我,虽然我看到的只是像头天晚上那样的黑暗中一只眼睛的微光,从我眼角一闪而过的影子……他们即使置身于这偏僻的山地,也很少在村庄和田地里现身,自从罗马人来了之后,他们就躲到人迹罕至的山岭和森林里,过着隐秘的生活。但我知道这些从未失去女神看顾的矮小民族就在那儿,他们一直照看着我。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