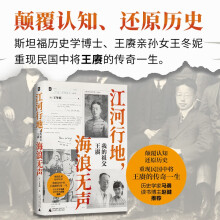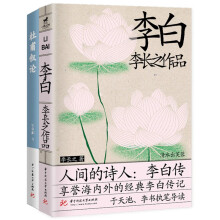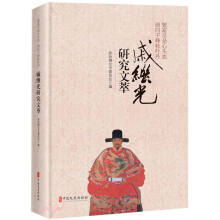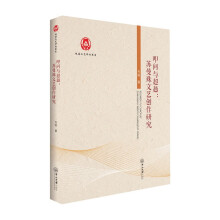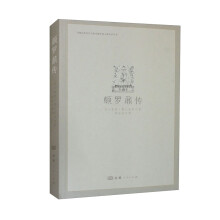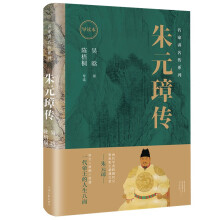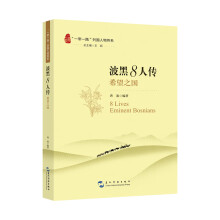《我在慈禧身边的两年》:
1895年我父亲出使日本的时候,我们曾在此“天后宫”有过一段不愉快的暂住经历,往事不堪回首,实在不想第二次踏进这同一条河流。虽然嘴上不说,父亲的考虑和安排,我们却无一例外地非常赞同。
“天后宫”风烛残年久已失修,即便金玉其外,亦难免败絮其中。当时有这样约定俗成的规矩,地方官应尽地主之谊,为途经本地的高级官员提供住所,照顾好生活起居。路过本地的高级官员也大可不必拒绝好意,只管安然受用便是。我父亲却总是婉言谢绝地方官的安排,情愿自行解决生活起居问题,以求身心安适不受拘束。
经过了一番奔波和忙乱,我们终于平安抵达侨民饭店。此时正有两封来自紫禁城的电报等着父亲,要求父亲马不停蹄赶往北京城。看似简单的命令其实难如登天,因为在这个季节里,通往天津的水路正逢冰冻,着实令人寸步难行。何况,我父亲年老体弱,疾病缠身,若没有医生悉心照料,实在难以撑得住舟车劳顿。若改道秦皇岛,那么一番乏味枯燥的长途旅行,更会让他体力难支,疲惫不堪。
鉴于这种种主客观困难因素,父亲不得不回电说,困难重重,实在难以即刻成行,恳请等到冰河溶解,便马上乘船北上,赶赴天津。
我们2月22日离开上海,26日顺利抵达天津。同当初抵达上海时一样,受到了当地道台和地方官员的热烈欢迎。
当时表达尊崇的规矩很奇特,从外国归来的当朝高官,船只在中国海岸停靠,上岸后必须照例执行“恭请圣安”的礼仪(即参拜天朝皇帝)。
以当地道台的资历,尚不具备主持“恭请圣安”这等礼仪的资格。好在我们抵达的时候,直隶总督袁世凯恰好身在天津。他安排了一名精明强干的随从与我父亲联络,并筹备好了“恭请圣安”的时间和地点,诸事齐备毋庸赘言。
我父亲与袁世凯恭恭敬敬地穿戴好朝服、朝珠、顶戴花翎,立即赶往专为此类仪式斥资兴建的参拜之地万寿宫。众多职位卑微的官员早已恭候于此。
我们到达的时候,直隶总督袁世凯和一些官员已经先到了。在这座半是宫殿半是庙宇的宏伟建筑殿堂中间,摆放着一只很长的窄几,安放了皇帝和太后的牌位,上书几个大字:“万岁,万岁,万万岁。”
“恭请圣安”仪式开始了,袁世凯立于窄几左侧,其他官员分立殿堂两侧。父亲进入大殿,径自朝前跪拜下去,高声说:“微臣裕庚恭请圣安!”随后询问圣体可好。袁世凯站在旁边代为回答说:“皇帝与太后圣体安康。”“恭请圣安”仪式到此结束。
我们一众人等在天津停留了三天,2月29日抵达了北京。我父亲当时身体状况不容乐观,无奈只得告假四个月,在家悉心诊治调养。他的恳求得到了慈禧皇太后的恩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