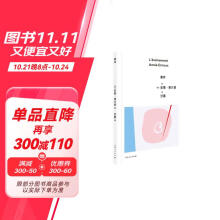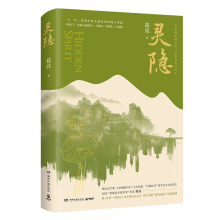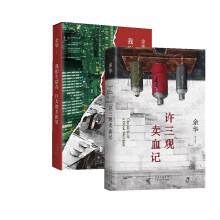白迷迷的古老官路,沿漳泾河由北向南,绕着绿竹蓊郁的须家宅悄悄打了个结,然后跳过河畔美丽的荷叶岛,逶逶迤迤地向着东南方遥遥在望的李王庄伸去。在广漠的田野里,这条路看起来那么纤细柔弱,欲断无力,好像飘向天际的一只风筝的细线,但同时它又是这样的坚韧顽强,把沿途的每一处村庄,每一株树木都牢牢抓住。它是一条敏感而忠实的导线,把无尽的欢愉和情爱从这个村庄传到那个村庄,也将人世间的仇恨和愤怒紧紧串联。
在春夜的寂静中,须家宅的人沿官路来到村南面的老柳树下,便会听见一种难以形容的极轻微的声音——有时是“扑通扑通”,有时是“咕噜咕噜”,仿佛鱼儿戏水,又似村姑洗衣,可水面光滑如镜。因此人们一口咬定那声音是从对岸荷叶岛上传来的。
岛上有座庙叫长庙。长庙是因庙跟前的桥而得名的——显而易见,这桥就是长桥了。
相传在太平天国闹革命时,这里的老百姓为躲避长毛的抢劫掳掠,人都跑光了。偌大的村庄,只剩下一个打鱼的孤女。
长毛进村时,孤女正在河边洗衣服。这孤女黑黑的眼睛,黑黑的脸庞,黑黑的浓发和小腿,却自有一种饱含着阳光和野气的动人魅力。几个长毛一见,淫心顿起,饿狼般扑过去,只见那孤女纵身一跳,便跃进了水里,鱼一样灵巧地朝那河中心的小岛游去。长毛不会水,急得在岸上来回跑,忽见一座桥,便不假思索地踏上去——这桥是通向小岛的,两边桥堍上,有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可就在这时,一股异香扑来,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脚踩两朵白莲,从银杏树顶上的天空里降下,指着急猴猴的长毛:“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便是逆天,从来逆天者亡!”
长毛气得“哇呀”一声怪叫,举矛便刺,却扑了个空。老者倏然消失,只剩下香犹可闻。长毛不理会,继续往前追。奇怪的是那小小的岛屿明明就在桥那头,可怎么也走不到。追了大约有一个时辰,人还在桥上,长毛心下疑惑:“怪了,这桥恁长!”抬头一望,却见那黑姑娘正在岛上晾湿衣服,裸露着轻盈盈的花朵身儿,紧揪揪的蘑菇奶儿,黑黝黝的肌肤滑腻如锦缎,真是活脱脱一条撩人的美人鱼!
长毛欲火中烧,越发不肯罢休,便一个劲往前赶,从日出赶到日落,从天黑赶到天亮,只是怎么也走不下这桥,怎么也跨不上那岛——后来,太平军全军覆没,那个曾向百姓多次许诺的天国,也如小岛上的黑姑娘一样,变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诱人梦境。惟有这桥,这庙,没有一天不以冷漠的沉默对峙着来自大千世界的纷乱骚扰。人们因此便把这桥称作长桥,把庙唤作长庙。
人们去荷叶岛大抵是为了到长庙烧香。据说长庙菩萨的金身,是一条黑鲤鱼变的——黑鲤鱼就是那个黑姑娘。每当残冬消尽,河上吹来的风懒洋洋地温柔起来时,黑鲤鱼耐不住寂寞,便在夜深人静时哨悄溜出来玩耍。那神秘的难以形容的声音就是黑鲤鱼发出的。
也难怪黑鲤鱼要在深夜出游,荷叶岛的美是一种深邃沉静的美,一种威严、冷漠的美。每逢盛夏,水面上绿叶叠翠,红白两色的荷花争娇斗艳,阵阵清香随风飘逸。这座形状酷似一张荷叶的小岛,被芦苇织成的绿墙封锁着,与世隔绝般的清纯、洁净。一株连一株的古老的银杏树,如参禅的和尚一样静默地站立着,在烈日当空时泼下清凉的浓阴,这份仁慈令人感动。
在银杏树掩映下的庙宇里,苍白的长明灯日夜闪烁着,关闭的门窗禁锢着永远沉寂的夜;香烟缭绕,菩萨被箍在这螺旋形的宝塔里——看不见花的色彩,也听不见尘世的喧嚣——当然寂寞难熬,渴望着外面那个活生生的世界了。
看来人和菩萨的心是相通的,虽然菩萨以威严的仪态俯视人类,人则无比虔诚地向菩萨顶礼膜拜。然而在那远古的时代,人在想像的天堂里塑造神秘的偶像时,就为自己铺设了一条单纯的小路。通过这条小路,人和菩萨都剥离了涂抹在身上的金粉和光圈,让心和心相见了。
因此,在历史的变迁中,菩萨的命运也和人的命运一样沉浮起落。太平盛世,庙里的香火自然是盛的;兵荒马乱时,人自家的性命都难保,庙里自然也就冷落了。不过,荷叶岛的香火完全断绝,只有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这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们忙着开会、斗争,喊高昂的口号,部署雄伟的计划。菩萨被敲碎了,脑袋浮在河里一漂一漂的。
近年来,庙宇又修葺一新,菩萨的金身也重新塑起了。现在的年轻人比过去的老工匠更讲究艺术,也更懂人体的比例,所以这新菩萨塑得魁梧高大,栩栩如生,眉宇间焕发出一种现代青年所崇尚的不折不扣的男性美。
这确实不大像一个菩萨。传统观念中的菩萨是慈眉善眼、丰满肥胖、不男不女的。然而奇怪的是并没有人对此发表异议,甚至连上了年纪的人也点头称赞:“唔,长庙的老爷又塑起来了,好,好!”或者相约着说:“啥辰光有空了,烧香去。”
这儿的人称菩萨为“老爷”。
须家宅新任的村长须明华皱起眉头把这老爷研究了半天:“据我所知,释迦牟尼是佛国第一位大神,是现世婆娑世界的教主;还有嘛,东方琉璃世界药师如来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过去佛燃灯,未来佛弥勒,以及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王菩萨……可这位‘老爷’,究竟是哪家佛门里的神,到底算什么菩萨呢?”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