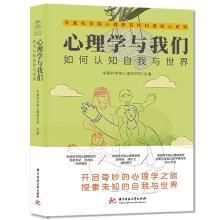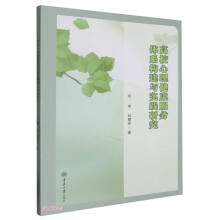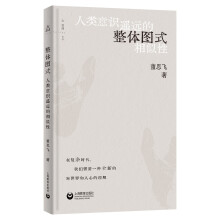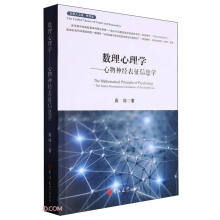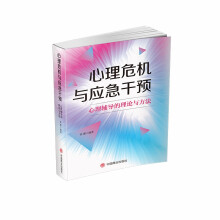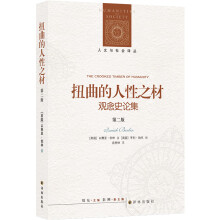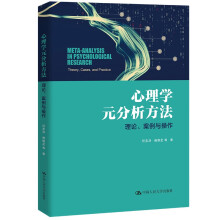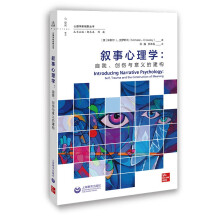第1章绪论及概要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刺激-反应关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现在,心理学研究正试图详细了解产生这些关系的认知过程的机制和内部结构。我们想在小范围内建立一个清晰的过程模型,以便依靠刺激材料中的信息产生所预测的行为。
这种对认知过程本身的关注,使人们开始重新寻找一定时间内增加观察频次的方法,以揭示这些过程的中间环节。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记录被试注视的方向(眼珠移动)、问题解决之前的中间行为(刺激材料的移动或对其各种操作)。由于对中间加工数据的收集与分析成本较高,仔细考虑如何正确解释这些数据,以及思考它们对我们理解该现象有何帮助,就显得十分重要。
收集认知过程信息的一种常用方法是,使用口头报告方法探究被试的内心状态。这类方法正是本书要探讨的主题。
1.1 使用口头报告:五个问题
如果我们要把被试的口头报告作为心理学实验的基本数据,有几个问题是必须要处理的。第一,我们必须回应过去许多心理学家对被试的口头报告是否适合作为科学数据所表示的强烈质疑。第二,我们必须考虑将被试的行为(无论是言语或非言语)转为数据需要进行的必要操作。第三,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将行为编码为数据,使之客观、统一,使得到的数据是“硬数据”而不是“软数据”。第四,我们必须明确指出编码过程中必然蕴含的理论前提。第五,我们必须指明从数据回到行为,再到对被试思维过程进行推论的过程。
在此,我们对以上五个问题加以讨论,它们将作为主题在本书中频频出现。
1.1.1 对口头报告数据的质疑
自从行为主义战胜内省之类的理论后,人们便对口头报告是否可以作为数据产生了怀疑。更确切地说,行为主义及其相关的学派对口头报告可否作为数据莫衷一是。一方面,按标准的实验范式,口头反应(或键控穿孔机,其在心理学上与口头反应难以区分,只不过它是用手指而非用嘴表示)可提供原始数据。在概念获得(concept attainment)实验中,实验者呈现一个可能的例子后,被试要说(或用手势表达)“是”或“不是”。在问题解决实验中,他们一旦有了答案就要说出来。在死记硬背学习实验中,当给被试呈现刺激音节“CEF”时,他们说“DAX”。通常衡量成绩的方式(反应时间和正确答案的数量)均基于被试的这些回答,而测试方式的准确与否则取决于被试是否讲了真话。
另一方面,现代心理学对被试解决问题或作答时的口头报告持怀疑态度。对于被试针对实验者的提问所做的回答或就先前行为进行回忆后所做的回答,这种疑虑更大。所有这些口头报告行为常常被斥为内省法的变体(Nisbett & Wilson,1977)。一般认为,内省法可能有助于发现心理过程,对于验证则毫无价值。正如拉什利(Lashley,1923)在抨击该方法时所说的常被引用的一句话—“内省法可用于初步调查,但之后必须用客观测试方法进行检验”。
1.1.2 从行为中提取数据
许多人认为口头报告可能会提供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但这些信息是非正式的,需要其他数据进行验证。该看法影响了口头报告收集与分析的方法。如果获得口头报告的目的主要在于提出假说与想法,研究者就没有必要去关心收集数据的方法(到目前为止,的确很少有研究者关心此事)。关于这些问题的文献很少,所用的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的差别很大,使用这类数据的论文对这些方法只是一带而过。
如果我们要在理解人类认知过程方面取得快速进展,这种状况完全不行。首先,目前尚没有明确的准则将不合理的“内省法”与常常被视为数据的各种言语输出区分开来。例如,在概念获得实验中,我们尚没有什么理论或实践依据将被试的“是”或“否”这种回答与被试称“自己当前想到的是小黄圈”这种回答区分开来。其次,对各种形式的口头报告尚未进行区分,如出声思维、对具体提问的回忆作答和受训过的观察者的传统内省报告,它们一起被笼统地贬为“内省法”。
1.1.3 “软数据”与“硬数据”
许多研究者称口头报告或口头描述为“软数据”,称简单的行为指标(如反应时间或回答的准确性)为“硬数据”。这种区分是什么意思呢?在科学中,数据与理论之间存在清晰的界限。数据应直接来自观察,理论则要对观察到的数据进行说明、解释和预测。当主体间一致认为这些数据与观测到的行为对应时,这些数据就是“硬数据”。
即使是倾向于心理分析或存在主义的心理学家也会将反应时间作为数据,尽管这些数据可能与解释行为并不相关。但如果分析人员将5秒的梦境描述编码为“口欲滞留”(oral fixation),许多心理学家会认为这段编码并非数据,而是对数据(即对梦的口头描述)的主观解释。当然,从口头报告中取得编码是需要大量理论推论的。只要数据含有这种推论,特别是当理论前提和推论规则本身并不完全清楚和客观时,人们就将这些数据称为“软数据”。“软数据”的问题在于,不同研究者会做出不同的推论,他们不能在编码方式上达成一致,每位研究者都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得出一种有利于其理论观点的解释。
硬数据、软数据的区分与口头和非口头的区分是不相关的。同样的推理问题也会出现在观察者对非言语活动(如身体运动的顺序、几段音乐)的理解中。与理解口头言语序列一样,这些非言语活动也同样需要解释。
技术的进步使我们可以将口头报告当作数据。在卡式录音机得到广泛使用之前,实验者一般对口头报告做摘录式笔记,用自己的话表述被试的话,省略一切“不重要”的内容。在对这些笔记进一步分析时,研究者不可能将被试的报告与实验者的推论区分开来。另外,由于编码中直接或间接采用的理论是用非常笼统的话表述的,这些口头报告的编码就更难以作为数据。研究者对一般机制的寻找也使他们仅对整个口头报告进行总体解释,而对各个口头报告语句的编码和说明并不关心。
近年来,基于认知过程的显性信息处理模型研究改变了人们对出声思维的看法。现在,标准的步骤是将磁带内容一句句认真转录下来,以便将原始数据以“硬数据”的形式保存下来。同时,认知过程信息处理模型为编码过程变得清楚客观提供了基础,这样研究者就可以对该过程的理论假设进行客观的检验。
1.1.4 编码中的理论预设
库姆斯(Coombs,1964)在其著作《数据理论》(A Theory of Data)中指出,原始数据从*初的观测,经由几个典型步骤,被编辑和编码,然后用于检验理论或做出预测。这些步骤并非不涉及任何理论,它们可用于处理口头报告数据,也可用于处理其他类型的数据。第一步,通过理论界定很小范围内的可观察的相关行为。这种相关性的判断决定了什么行为要记录下来。第二步,再次根据理论对这些行为进行编码。
就言语行为而言,这种过程始于录音,录音中包含实验期间几乎所有的声音。在转写磁带内容时,研究者需要做一些选择。时间信息、重复和重音在用来分割和解析声音流之后,这类信息中的多数通常会从转录本中删除。我们将转录这一步称为“预处理”。
下一步,对于预处理后的片段,使用理论模型中的术语进行编码。通常要事先确定编码类别,然后让人对编码进行评估判断。如果每个片段都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数据,那么该片段的编码必须根据其中包含的内容来进行,独立于周围的片段。在本书第6章,我们将用较长的篇幅讨论这种本地编码的方法,以及必须要满足的条件。
使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对口头报告进行分析:一种方法不需要分析意义,而另一种则需要分析意义。在第一种分析方法中,被试与实验者事先约定一些具体的信号(可以是语言信号或按键)以进行沟通。这些信号大多是随意的,如被试可以使用“cef”来代替“yes”。被试与实验者之间的沟通只是因为彼此间的约定才成为可能。要在这种条件下分析口头报告,实验者必须将每个语音信号划入约定类别中的一种。仅从理论上而言,编码者根本没必要知道被试的语言,以确保不会对推论进行有意义的分析。心理学中的很多范式都使用这种分析方法,例如,使用量表与多项选择的研究都可以被看作使用这种方法的实例。
在第二种分析中,对观测到的口头报告要按其意义进行分析。即使如此,分析方法背后的理论只是将编码限制在口头报告的某些方面和特征,而非全部意义。例如,在一项典型的概念获得研究中,每一案例或刺激可以表示为各特征的一个独特组合,每个概念可以表示为这些特征的某种独特配置。接着,编码简单要求将口头报告映射到这些概念与特征,这时一般不会出现模棱两可的情况。尽管从逻辑上讲不同的概念非常多,但与自然语言的可变性相比,这些概念的数量还是很少。因此,对“红色的圆圈是cef”这样一句口头报告的编码方式与对“血色的圆环是cef”的编码方式是相同的。
具体的理论与实验会大大限制可取解释的范围,使研究者对口头报告只能进行选择性分析。如果一个概念获得理论局限于假设类语言,许多口头报告内容将不会被编码,如“不知道该做什么,这个我就猜猜看吧”。这种类型的有关意义分析的例子很多。在这些例子中,口头报告内容被映射至事先决定的正式类别中。金托什(Kintsch,1974)和其他学者曾对有意义文本的记忆进行分析。纽厄尔和西蒙(Newell & Simon,1972)分析过一些实验,识别出一些明确的知识状态,据其可以对被试的出声思维内容进行编码。
许多口头报告分析不适用于上述方案,包括多数试图理解口头报告内容的分析。在不太正式的分析中,编码方案并不是从形式上事先加以规定的,而是寻求解释与寻求合适的模型或理论同时进行。我们认为在新领域内可以一边寻找理论一边制订编码方案,但在这里,我们将主要论述在实际编码开始前已确定好理论术语的情况。
1.1.5 从行为中推导思维过程
有时人们认为,使用口头报告数据意味着接受被试的自我解释和对所报告事件的解释。这是一个信任问题,源自我们的日常经验和语言使用。为与他人进行有效沟通,我们会相信他人的话。如果有人说他刚买了一辆新车,我们一般会信以为真,而不是让他出示销售合同或发票。与此类似,我们相信别人(至少相信自己的朋友)会正确回答问题,并给我们*好的建议。但是,如果这个问题对我们很重要,或者怀疑对方有不可告人的动机,我们或许会让对方提供更多细节,来审视我们手头所有的证据,这同样适用于科学研究。很少有科学家不对证据进行独立审查便接受另一位科学家关于找到有关超感觉的确凿证据的说法。
被试有关自己心理状态和思维过程的口头报告导致的信任问题略有不同。根据一种朴素的意识理论,唯有被试本人才对自己的心理状态和思维过程有着直接的了解。被试往往相信自己能够如实地报告自身的心理体验。出于很多原因,实验心理学家对此并不认同,他们证明在许多情形下这种自我报告是不可靠的。
然而,自我报告的可靠性问题可以(我们认为应该)完全避免。被试报告“X”,研究者不必以此推断“X”是真实的,而只需认为被试能够说“X”(即拥有使他能够说出“X”的信息)。如此一来,我们甚至可以说,被试被信任的程度与他们报告内容的数量成反比。因为他说得越多,研究者就越难建立一个会产生这些反应的模型,所以我们对能够预测这些反应的模型就越有信心。
比如,以下为实验者与被试间的对话:
1. —你知道瑞典首都是哪里吗?—知道。
2. —下面三个城市,奥斯陆、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哪个是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
3. —说出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
4.(关于被试是如何回答第1题的回溯式口头报告的):首先我努力想象瑞典在欧洲地图上的位置,这时奥斯陆出现在脑海中,但我记得它是挪威的首都。接着,我想到了斯德哥尔摩,记得那是颁发诺贝尔奖的地方,接着我确信可以回答“知道”。
在第一个例子中,如果我们想推断该被试真的知道瑞典首都,就不得不相信他。在第三个例子中,除非他能回忆起来,否则不可能说出正确的名称。第二个例子和第三个例子的主要差别在于,在第二个例子中,被试有可能是回忆,也有可能是猜测或其他情况。第三个例子为回溯式口头报告,表明被试的记忆中有这个名称,同时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