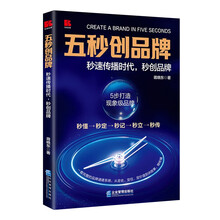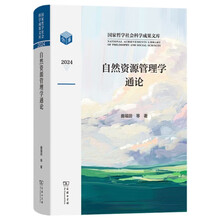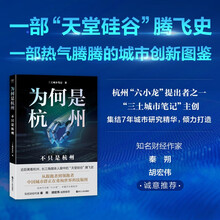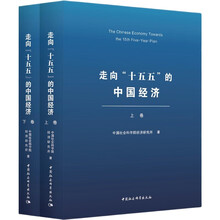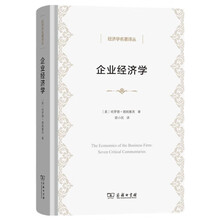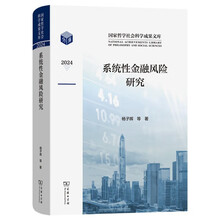第1章 绪论
1.1 信息爆发带来统计需求
网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句话更确切的解释应该是信息产业技术改变了我们的生产、生活、消费乃至于我们的生活习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信息技术对世界的改变是巨大的。人们*初认识到这种变革的力量是在20世纪中叶,美国学者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先给它起了一个名字——知识产业,并对知识产业展开了*初的测度,其后波拉特(Marc U.Porat)、小松崎清介等众多的学者展开了对知识产业(或称信息产业)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对信息产业的研究达到了顶峰,这是由于在这个时间段美国出现了“新经济”现象。“新经济”现象主要表现为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高股市成长,这种打破传统经济规律的新现象的吸引力简直是无穷无尽的。世界各国都开始研究“新经济”产生的原因,“新经济”的运行机理等问题。理论界对“新经济”现象的研究热情也空前高涨。当然“新经济”产生的大多原因*终被归结于信息技术的发展。
从信息技术进入经济学家的视线到轰轰烈烈的研究,不同研究者或者研究机构给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经济现象、经济模式、产业形式以不同的命名,有的称之为“信息革命”,有的称之为“后工业时代”,有的称之为“后服务社会”,有的称之为“计算机社会”,当然更为普遍的称呼是“信息经济”“信息产业”“ICT产业”(信息与通信产业)、“知识经济”等大家更为耳熟能详的名字。
关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经济变革到底叫什么其实无关紧要,本书认为当我们把信息带来的变革提升到经济模式的层面,以“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称之可行;当我们把信息理解为一种产业层面的变革,那么称之为“信息产业”或者“ICT产业”也可行。
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虽然晚,但是其速度却是让世人瞩目的,尤其是在近十年来,中国信息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堪称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现在,网络交易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使用网络购物的用户规模高达4.67亿人,“网上订外卖”“预订旅游”“移动支付”及大量诸如“共享单车”“自媒体”等基于信息技术发展的“互联网+”产业大量涌现,这些新兴行业方便、丰富了群众生活,也产生了巨大的市场。信息产业在中国的发展走在了“快车道上”。
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会议上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 ,激起了全民创新创业的热情,随后经济学家观察到创新、创业的热点领域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信息产业领域。“互联网+”成为*火爆的热点领域,用网络去升级改造传统产业,用信息去提高效率成为这一波创新创业浪潮的主题。尽管没有权威的数据去证实中国信息产业发展的水平,但是我们已经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在20年前我们说的信息产业具有高度的“渗透性”,如今在中国变成了现实——我们很难再找到一个游离于信息技术之外的产业了。
中国在信息产业的发展中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随之而来的是关于信息产业数据的大量需求,然而面对这样的新兴产业,统计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都还不充分。在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统计工作是以SNA为中心框架进行的。而SNA体系本身并没有单独将信息产业进行核算,中国的产业分类也没有明晰的信息产业分类标准。信息产业的巨大数据需求与有限数据供给之间的矛盾导致了信息产业数据一定程度上的混乱(数据质量低、可得性差、口径各异等)。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信息产业统计理论的不健全。因此,如何提供高质量、高时效性、翔实的信息产业数据成为广大统计研究者和统计工作者面临的严峻问题。
1.2 “新现象”挑战传统核算方法
中国官方统计是在SNA框架下进行的。在现代经济模式下,SNA体系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统计体系,SNA在核算内容上较为全面,能够全面地描绘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在核算方法上SNA比较科学,复式记账法和权责发生制的记录原则能够保证数据的高质量和关联性;生产范围的确定较为合理,在“该测度”和“可测度”之间选择了一个较为理想的契合点[SNA的生产范围包括所有的货物生产、知识产品的生产(住户自给性知识产品的生产除外)及为他人提供的服务的生产(还包括自有住房者的自给性生产和付酬家庭和个人服务)];此外,在交易时间、交易价格等方面SNA都有较为明确、科学的确定方法。可以说,中国采用SNA框架进行经济核算是统计工作的一大进步。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信息产业飞速发展的这些年,给整个经济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也让始建于1953年的SNA框架在某些领域逐渐失效。尽管SNA体系自身也在不断进化,但是我们观察到,即使按照*新修订的《〈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2008 SNA)》的核算框架,一些经济现象仍然难以被囊括进SNA体系。
1.2.1 网络成为生产者的“前台”
O2O(online to offline,在线离线/线上到线下),是指将线下的商务机会与互联网结合,让互联网成为线下交易的平台,这个概念*早来源于美国。O2O在中国的发展可谓是如火如荼,网上交易的范围在不断扩展,大到家具家电,小到柴米油盐,网络购物已经成为人们购买行为发生的主要形式;生活缴费、话费充值、线上打车租车、预约按摩,人们的服务需求也可以在网络端实现。智能手机的普及更是让O2O在中国国民的生活中扮演了主角,一部手机几乎可以解决人们衣食住行的所有问题。
对消费者来说网络是消费的入口,对生产者来说网络就是重要的销售“前台”。互联网跨地域、无边界、海量信息、海量用户的优势在O2O模式中集中体现出来,在理论上生产者通过网络可以直接与所有的网络消费者进行直接接触。网络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传统的商业渠道,电商平台已经成为众多商家*重要的销售渠道。众多中小企业依靠网络进行销售,传统的大型企业也开始纷纷开设自己的网络旗舰店或者开发自己的线上销售平台。
1.2.2 网络提高了生产的效率
生产者的分工一直在细化,信息技术让这一分工过程进一步加速了。网络端口既是销售的端口又是售后和其他服务的窗口,网络是消费者与企业联系的唯一纽带(为了方便行文我们把网络服务端称为窗口部门)。窗口部门的重要性在整个生产和销售环节变得更加重要。
在现实中窗口部门不一定是产品生产者的一部分,其实在改革开放发展到纵深阶段,许多企业的终端销售业务已经开始逐渐剥离(尤其是中小企业),产品的生产者往往不再直接面对消费者,网络的存在既让窗口部门的销售有了几何级增长的可能,大量资金的积累得以实现;同时来自网络端口的大量数据成为窗口部门掌握的巨大财富。窗口部门掌握了销售渠道,窗口部门*清楚消费者的需求,窗口部门还掌握了大量的资金,这三个基础条件让窗口部门的“独立性”进一步加强。这种“独立性”让窗口部门从生产的销售和售后服务部门逐渐向生产的主体部门转变:产品的设计、产品的研发、产量的确定、产品的定价等传统的产品生产者的职能开始被窗口部门吞并,产品生产部门逐渐变成“生产的机器”,产品生产部门只需要执行窗口部门的“指令”即可。
窗口部门掌控生产,从效率角度来讲是一个进步。信息技术让窗口部门的决策更加“正确”:*先,产品设计的针对性更强了,用户数据的支持能让窗口部门设计出针对不同消费者的多样化的产品;其次,产量与价格制定更为精准,抛开商业伦理和公平,大数据支持下的产量制定和定价策略将更为准确,甚至可以实现经济学中的“一级价格歧视” ;*后,在剥离了销售、售后服务、产品设计、产量制定和价格确定等众多职能后,产品生产者专注于生产,更有利于生产领域的效率提升。
1.2.3 网络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力量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机制是资源配置的主角。在信息经济时代,消费者的消费过程和偏好依然没有根本上的改变,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在信息经济时代,由于获得信息的搜寻成本更低,价格的传导机制更加灵敏。在信息经济时代,价格作用资源配置的过程将发生新的变化。
生产成本低、生产效率高的生产者在网络背景下的市场竞争中将获得更多资源。在信息经济时代,生产者的价格信息、产品信息更容易被消费者识别,“赢者通吃”的情况更容易发生。窗口部门作为生产的“大脑”,可以通过更为便捷有效的方式扩大生产规模——它们只需要向不同的工厂下单即可扩大生产规模,传统经济学中的规模经济规律在网络时代将发生改变 。因此,未来大企业将会更容易出现,垄断更容易产生。
1.2.4 生产的概念更加模糊
SNA将生产的范围定义为为他人提供的货物或服务 ,SNA生产的范围就是核算的范围。但是在近几年信息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经济现象符合SNA对生产的描述却难以纳入核算的范围:
(1)自媒体、网络直播、视频网站及其他应用软件中大量由住户部门发布的信息、音频、视频等内容。这类内容在性质上满足“为他人提供的服务”这一条件,而且这类内容与一般影视作品、新闻消息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这类内容其中一部分以获取收益为主要目的(如网络主播,收费的视频、音频等),更大的一部分是以分享为目的的。以获取收益为目的的因为存在“市场交易”,所以理应也能够被纳入核算范围,但是以分享为目的的,由于难以计算价值,且数量巨大,在技术上很难被纳入核算范围。
(2)从分享到盈利只有一步之遥。以分享为目的的信息、视频、音频制作,一旦获得足够的关注度,制作者就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实现盈利,这种从“分享”“兴趣”向营利性、职业性的转化几乎可以瞬间实现。
这些情况让经济统计核算陷入了两难境地:执行生产范围的界定,核算有困难;重新拟订修正生产的范围,传统行业的生产范围是否也需要一起改变。
1.2.5 经济成本与经济效果不匹配
知识产品(也译为知识载体产品)是指那些以消费单位可以重复获取知识的方式而提供、储存、交流和发布的信息、资讯、娱乐等。知识产品是《〈2008 年国民账户体系〉(2008 SNA)》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在对经济现象的观察中,我们发现知识产品往往能带来更多更大的经济效果。例如,在知识分享、在线教育等论坛或APP(application,应用程序)中,一门课程往往会获得几十万甚至更多的订阅,换句话说,从经济效果上来说,相当于一名教师直接向几十万人授课,而其经济成本则与给一个标准班(30人)授课的经济成本并无多大差异。如何衡量这类知识产品是SNA面临的一个难题,如果说一部分收费的课程按照SNA的市场原则核算还算可行 ,那么大量的免费的,但是经济效果相同的资源又该如何核算?
1.3 未来的经济核算
与十年前相比,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十年前我们绝大多数人对于“外卖”是陌生的,而2017年外卖订餐人数规模则超过了3亿人,市场规模超过了2 000亿元;十年前,我们没有网络直播、没有短视频,2017年短视频的用户规模达到2.42亿人,网络直播用户数量达到4.22亿 网络创造着消费,网络刺激着消费,在SNA中以前因为规模过小而不值得核算的领域可能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会变成一个让我们无法忽视的庞然大物,SNA还能应对这种变化吗?我们的官方统计应该何去何从,这是我们今天不能不严肃面对的问题。
1.3.1 未来:新的经济模式的核算
杨仲山和屈超(2009)认为:“考虑到未来的经济预期,网络可能会全方位彻底改变我们生活的经济社会,而这种影响远远不可能仅局限于一个产业的影响。互联网作为一种影响未来经济的力量,信息经济实质是一种经济模式,而这种经济模式应是区别于传统工业社会的经济模式的。”从经济模式的角度来看,目前信息经济的发展已经展现出彻底改变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强大力量:信息技术已经开始渗透进几乎所有的行业;人们已经不再谈论“自动化”办公的话题,因为自动化办公早已全面普及;企业经营过程中的流程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已经高度依赖于相关管理软件;网络购物、移动通信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离开了网络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娱乐;就连离“信息技术”*远的农业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