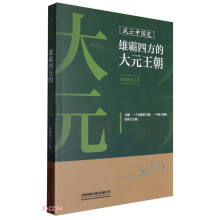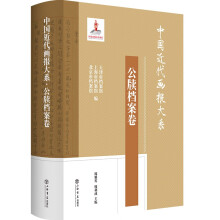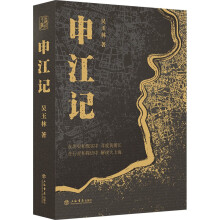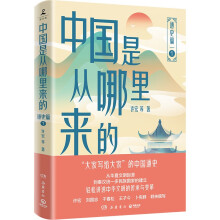我三岁的时候,父亲故去了,家里的生活是每况愈下,全靠着母亲辛勤的操劳维持我们全家的生活。我六岁那年,经人介绍投入荣蝶仙先生门下学艺,写了七年的字据(字据上注明七年满期后还要帮师傅一年,这就是八年,开始这一年还不能计算在内,实际上是九年的合同;在这几年之内,学生一切的衣食住由先生负责,唱戏收入的包银戏份则应归先生使用,这是当时戏班里收徒弟的制度)。
在我投师之前,我母亲曾不断地和我商量,问我愿意不愿意去?受得了受不了戏班里的苦?我想我们既不是梨园世家,人家能收咱们就不错,况且家里生活那样的困难,出去一个人,就减轻母亲一个负担,于是我毅然地答应了。
还记得母亲送我去的那天,她再三地嘱咐我:“说话要谨慎,不要占人家的便宜,尤其是钱财上,更不许占便宜。”这几句话,我一生都牢牢地记着,遵循着她的遗教去做!
荣先生看见我以后,认为这个小孩不错,当时就想收留我,这时我母亲就像送病人上医院动手术一样签了那张字据,从那天起,我就算正式开始拜师学艺了。
我拜师后的头一天,就开始练起功来,从基本功练起,当时先生还不能肯定将来会把我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才,只好叫我先和一些“试班”的学生一起练练功,开始从撕腿练起。
初学戏的人练撕腿,的确是一件很痛苦的事,练习的时候,把身子坐在地上,背靠着墙,面向外,把腿伸直撕开,磕膝盖绷平,两腿用花盆顶住,姿势摆好后,就开始耗起来。刚练习的时候,耗十分钟,将花盆向后移动,第二天就增加到十五分,以后递增到二十分、三十分,练到两条腿与墙一般齐,身子和腿成为一条直线,才算成功。开始练的时候,把腿伸平不许弯曲,到不了几分钟,腿就麻了,感到很难支持。与练撕腿的同时,还要练下腰、压腰。这种功,乍练起来也不好受,练的时候要把身子向后仰,什么时候练得手能扶着脚后跟,才算成功。练下腰最忌讳的是吃完东西练。学戏的练功,全是一清早带着星星就得起来练,不论三伏三九,全是一样。有时候早晨饿得难受,偷着吃点东西再练,但是当一练下腰的时候,先生用手一扶,就会把刚才吃的东西全吐出来,这样就要受到先生的责罚。先生常说:吃了东西一下腰,肠子会断的。
当我把这两项功夫练得稍稍有些功底时,先生又给我加了功,教给我练习较大的一些功夫了。练虎跳、小翻,抢背等功课。起初,一天搞得腰酸腿痛,特别是几种功课接连着练习;冬天在冰冷的土地上,摔过来,翻过去,一冻就是两三个钟头,虽然练得身上发了汗,可是当一停下来,简直是冷得难受极了。
将近一年的光景,一般的腰腿功差不多全练习到了,我还和武生教员丁永利先生学了一出《挑滑车》。
这时候荣先生准备让我向旦行发展,他请来了陈桐云先生教我学花旦戏。那时候花旦戏是要看跷功的,所以先生又给我绑起跷来练习。绑上跷走路,和平常走道,简直是两回事,的确有“步履维艰”的感觉。开始练的时候,每天早晨练站功五分钟,十分钟,后来时间逐渐增加了,甚至一天也不许拿下来。练完站功后也不许摘下跷来休息,要整天绑着跷给先生家里做事,像扫地、扫院子、打水等体力劳动的工作,并不能因为绑着跷就减少了这些活。记得那时候徐兰沅先生常去荣先生家串门,他总看见.我绑跷在干活。荣先生的脾气很厉害,你干活稍微慢一些,就会挨他的打。
荣先生对我练跷功,看得非常严,他总怕我绑着跷的时候偷懒,把腿弯起来,所以他想出个绝招来,用两头部削尖了的竹筷子扎在我的膝弯(腿洼子)上,你一弯腿筷子尖就扎你一下,这一来我只好老老实实的绷直了腿,毫无办法。这虽等于受酷刑一样,可是日子长了,自然也就习惯了,功夫也就出来了。
一边练习着跷功,一边和陈桐云先生学了三出戏,一出《打樱桃》,一出《打杠子》,一出《铁弓缘》。这时候荣先生又加上教我头本《虹霓关》中的打武把子。打武把子最讲究姿势的美,在练习的时候,就要求全身松弛,膀子抬起,这样拿着刀枪的两只手,必须手腕与肘灵活,才能显着好看。我在练习的时候因为心情紧张怕挨打,起初两只膀子总是抬不起来,为了这样的确没少挨荣先生的打啊。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