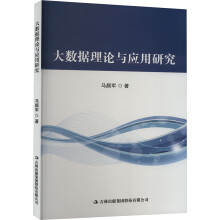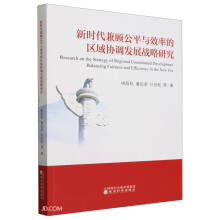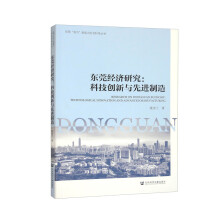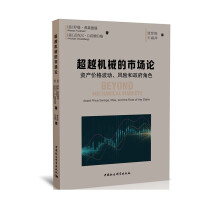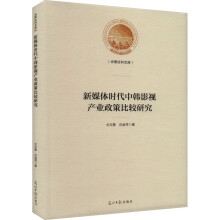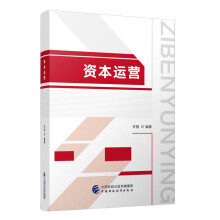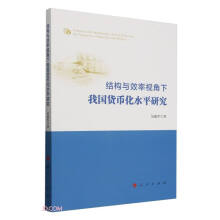第一章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医疗技术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健康意识的增强,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已经成为全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图1.1),1960~2020年,各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整体上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1960年的52.3岁提高到2020年的72岁。其中,中等收入国家人口预期寿命从45岁提高到72岁,而高收入国家人口预期寿命则是从68.5岁提高到79.7岁,60年间,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预期寿命的增幅分别达到27岁和11.2岁。进一步结合我国的情况来看,1960~2020年,我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已从43.7岁快速提高到78.08岁,预期寿命的增幅接近35岁。而且,近年来,我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已经超越了中等收入国家以及世界平均水平,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也从1960年的24.8岁逐步缩小到1.6岁。对比之下,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速度明显更快且增幅更大。
人口预期寿命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核心指标之一。预期寿命延长是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反映,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同时,预期寿命延长又是一把双刃剑,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风险与挑战。从我国的现实来看,一方面,我国人口预期寿命超越了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并快速追赶上了发达国家,这无疑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个人、家庭和社会享受到了长寿带来的红利。但另一方面,预期寿命延长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也会引发劳动力资源短缺、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养老负担日益沉重和公共财政压力上升等诸多问题。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截至2021年,我国人均GDP水平为12 551美元,尚未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在“未富先老”的形势下,长寿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风险与挑战可能更大。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应对长寿带来的风险与挑战是微观经济主体和宏观经济运行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政府与学界需要认真思考长寿所引发的经济资源如何合理调整和配置,以及这种资源的调整和配置所产生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效应。从微观个体角度来看,一方面,预期寿命延长会使人们面临更长的老年期,养老资源可能存在不足的风险,因此理性个体可能会对自己不同年龄阶段的生育、消费、储蓄、退休等决策进行调整,以优化生命周期内的资源配置,主动去化解长寿风险,同时微观个体行为的改变又会影响宏观层面的物质资本的积累、劳动供给和就业,从而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寿命延长意味着人们可以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工作年限也可以相应延长,从而能够获得更高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而且,随着人们受教育时间的延长,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技能结构得以优化,从而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经济增长。但由于教育年限延长也意味着教育投资成本的增加,预期寿命延长可能导致人们增加储蓄以备未来养老,减少对子代的教育投资,从而可能对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从宏观层面来看,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会加速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造成劳动供给总量和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持续萎缩,使劳动、资本等不同生产要素的相对回报率发生改变,进而对收入分配、技术创新以及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在养老保险体系上,由于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建立在高生育率和低预期寿命的背景之下,长寿风险可能导致养老保险体系的收支平衡难以为继,养老金支付可能会出现巨大的缺口,政府将面临沉重的财政负担,如果不能及时调整政策去积极应对,那么现行养老保险体系将难以为继,其保障和收入再分配功能将失效,个人和社会福利会受损。在资本市场上,虽然近年来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入市工作在有序推进,一定程度上把部分长寿风险分散到了资本市场当中,但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尚未完善,且政府和相关金融机构对长寿风险的分散与管理缺乏经验,养老金的投资收益率并不高,优化资产配置的功能也未能充分发挥,目前仍然面临着如何拓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领域、提高投资回报率、实现保值增值目标等方面的严峻考验。
由此可见,如果不能有效分散或管理潜在的长寿风险,根据预期寿命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来及时采取综合改革措施,那么在人口预期寿命提高和传统人口红利窗口逐渐关闭的情况下,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准确把握长寿风险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和作用路径,厘清长寿风险的宏观经济效应是推动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和化解长寿风险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大趋势下,长寿风险必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伴随我国的经济发展,这便需要我们及时调整相关政策,以更好地应对日益累积的长寿风险,促进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然而,目前的研究尚未从理论层面系统性研究预期寿命延长对储蓄、生育、人力资本投资、老年劳动供给、劳动生产率、收入不平等、养老金收支与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等宏观经济方面的影响效应与传导机制。本书将预期寿命延长引入理论模型的分析框架,将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响应有机结合,探讨预期寿命延长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机理,这不仅为我国应对未来长寿风险的挑战以及制定长寿风险管控措施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相关研究的外延边界,丰富了人口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风险管理理论。
第一,预期寿命延长会通过影响储蓄,改变物质资本积累水平,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根据生命周期理论,理性行为人在老年期往往是进行负储蓄,即消费较多而收入较少,在预期寿命延长导致老年人口比重提高的情况下,储蓄率可能会随之下降;但是,预期寿命提高后,健康余寿的不确定性增加,人们可能面临更大的长寿风险,“未雨绸缪”的储蓄动机更强烈,从而也可能使储蓄率上升。以往的研究聚焦于人口寿命延长带来的负担效应,即在预期寿命与实际生存年龄相等的前提假设下考察经济增长的变化,而忽略了实际生存年龄可能超出预期寿命所带来的效应。因此,本书尝试从理论上分析这两种不同效应的共同作用如何影响储蓄以及经济增长,为已有研究提供有益的补充。
第二,预期寿命延长会通过教育融资模式改变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预期寿命延长后,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老化,使得传统依靠人口数量与结构优势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人口质量尤其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与积累的重要方式,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家庭养老负担加重,不同教育融资模式可能会对家庭教育投资决策产生不同影响,*终影响到人力资本积累。本书将市场教育和公共教育融资模式引入理论模型进行分析,揭示不同教育融资模式下预期寿命延长对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为从教育融资视角制定应对长寿风险的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第三,预期寿命延长和生育政策的调整会通过影响家庭教育投资来影响经济增长。从理论上看,子女具有家庭耐用消费品和投资品的双重属性,在生育数量受到限制的情况下,父母出于利他或利己动机会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当生育限制放松后,子女数量增加既可能促使家庭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又可能因子女质量-数量的互替效应,降低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当预期寿命延长时,养老负担的加重既可能促使成年父母减少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又可能促使成年父母提高子代培养质量以获得更多的养老资源从而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放松生育政策的目的是应对人口老龄化与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本书将预期寿命延长和生育政策放松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理论上探讨放松生育政策能否对冲预期寿命延长带来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能够为完善我国生育政策设计提供政策启示。
第四,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持续延长的情况下,劳动人口年龄结构会加速老化,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理论上看,年龄的变化本身会引起个人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老年劳动力的身体素质和认知能力都处于衰退阶段,在劳动力年龄结构日渐老化的情况下,生产率水平会趋于下降。然而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人们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身体机能衰退和认知能力下降的年龄都可能会推迟,劳动生产率并不一定迅速下降。基于此,本书考察了预期寿命延长如何影响年龄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与预期寿命水平较低时的情形进行对比,从而补充预期寿命延长如何影响劳动生产率的经验研究,同时也为我国老年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开拓“第二次人口红利”提供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
第五,在预期寿命延长和劳动年龄人口结构持续老化的情况下,老年劳动供给对经济增长显得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和人均受教育时间均显著提高,但实际退休年龄却不升反降,呈现出提前退休的趋势。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这不仅会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也不利于老年人力资本的有效利用。为此,本书通过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框架下的世代交叠模型,考察预期寿命延长对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退休年龄选择的影响机制,并结合养老保险制度设计考察了预期寿命提高对老年劳动供给的影响,从理论层面分析并解释了在寿命延长的情况下人们提前退休这一反常现象,进而为如何提高老年劳动参与和提高人们延迟退休的积极性提供政策参考。
第六,预期寿命的延长会通过生育政策调整、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影响收入不平等程度。从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出发,本书将预期寿命延长和生育政策调整结合起来,考察两者如何共同影响我国的收入不平等;
展开